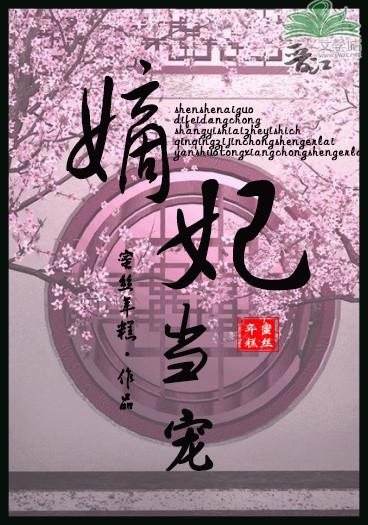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与帝为夫 十一公子 > 077尸体不重还有什么重(第1页)
077尸体不重还有什么重(第1页)
介意?怎么会呢……安宁转身先行带路,余光掠过婢女阿三惊慌未定的脸,思路反而清晰了,果然在上楼梯时,唐宕就趁红姨不注意落在了最后,等大家行到二楼,他身形一偏,立刻消失在楼道间……
宋季北早在红姨吃完饭就招呼不打一声走了。
如此到安宁住的房间门口也就她和红姨,外带女婢阿三。
“等下,我先进去看看。”安宁虚拦了一把红姨,然后径直先推门进去。
门没合上,红姨却识趣的等在外头,只是很快就等出结果了——
安宁从房里冲了出来,发出乒乓作响的声音,红姨听得声响,讶然不已,就见到安宁动作略急,面色慌乱。
“怎么了?”
“他没撑住。”
“什么叫没撑住?”
“死了。”
“啊!”阿三发出短促的一声惊呼,被自己捂住嘴巴堵住了,她本就受了惊吓,这会儿更是面色惨白。
红姨一怔,随即面色带霜,连忙进了那房间,幼白身上盖着一床皱巴巴的被子,满是血迹,红姨抖着手去探他的呼吸。
“没——没气了。”红姨收回手时反身去瞪阿三,厉声道,“你上来看他时,可还有气?怎么突然就死了!”
“我、我不知道,我看见被子床单上都是血……我就吓的跑出来了。”阿三一双眼都憋红了,双手也是抖个不停。
而此刻,装死的幼白憋着气,一股子血腥味刺激着他的鼻端,他不得不咬紧牙关屏息等待,唐宕这家伙哪找这么多鸡血。
红姨没探到他的气息,加上阿三的说辞,安宁一个劲的在原地转圈,显而易见是拿不定主意了。
“我今年真是遇上了灾星。”红姨并无太多惊慌,愤怒居多,大抵无缘无故摊上这么个事太倒霉了。
“怎么办?”安宁问她。
红姨一咬牙,“用个草席卷了,扔到山头的乱葬岗去,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安宁好似就等她这句话,飞快的从怀里掏出两锭足二十两的整银,还有一张银票,“一切有劳红姨你了,我,我就先离开了。”
她像是有人在屁股后面追一样逃出了那房间,根本不等红姨阻拦,她不过是个过路客,一走了之再好不过了。
红姨转头看了眼床上,凌乱而血迹斑斑的真是被糟蹋的不像样了,她把银子收起来,“怎么死了一个又一个,晦气死了,我真是造什么孽了?”
“那,那要扔吗?”
“当然要,去橱里拉张席子出来,等会把后院的马车赶出来,我来驾车。”
阿三去取了草席过来,哭丧着脸,“会不会是报应啊?”
“胡说八道。”
“可是,可是自从死了那个人以后……我们这就没再安宁过了,老板娘,要不还是去报官……”
红姨抬手就朝她头顶敲了一下,“要是让衙门知道人死在咱客栈,我们也被怀疑害死他的,一起被抓了砍脑袋,你还要去禀报吗?再说这小地方死人人家还不定会管……”
这小镇上没有官府衙门,还要去十多里外的大镇上报官,来回也要一天了。
“那,那怎么办?”
“快点卷起来,这个男人估计也没什么身份,快点去扔了,没人会知道。”
被草席包的乱七八糟的幼白暗自叫苦,这么躺着装死人挺尸还真是件痛苦的事,草席一卷更是气闷,他又不能大口喘气。
等阿三牵了马车出来,好在天真的全黑了,阴雨绵绵的也没人,红姨亲自动手帮着阿三一起把包着幼白的草席一前一后搬上了马车。
阿三还是极度害怕,“怎么这么沉?”
“尸体不重还有什么重。”红姨骂她一声。
“老板娘,为什么不叫阿二一起帮忙……”
阿二就是红姨的另一个女婢,人长的粗壮些,多干重活累活,常年在厨房里待着的。
“那丫头看着憨壮,心眼不晓得多鬼。”红姨自然是不想多一个人知道多份风险,阿三人小胆儿也小,也听话的紧。
拉上马车的门帘,红姨知道以阿三的胆色她根本不敢把人往乱风岗丢,所以她不得不让阿三留下去收拾楼上的残局,自己坐上了车前的隔板,“我马上就回来,你把那房间收拾干净,一切都当没发生,像上次一样,听见没有。”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