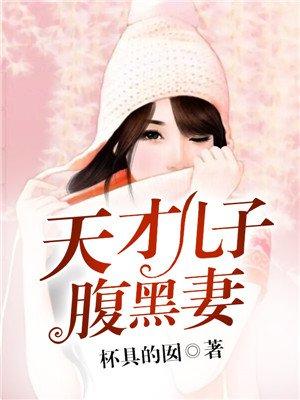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红楼第一梦指的是什么 > 第37章(第1页)
第37章(第1页)
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泪水汹涌而下。
“来人,取鞭子来。”骑虎难下的贾政无法,要让大老爷出气,只得拿自己儿子出气。
“又挨打了?”辰元殿的书房,元辰从奏折后抬起头,蹙眉看着暗卫甲。
“是,殿下,虽然伤得比那次轻,但这位公子看上去却病得厉害,贾府那位大老爷也太过份,自己行为不知检点,还跟一个后辈刻意地过意不去。”暗卫甲想到贾赦泼皮不饶人的劲,为那位心神俱创的公子辩护道。
“放肆。”元辰摔了手中奏折,眼神冷咧,怒容满面。
暗卫甲低头:“属下枉议,罪该万死。”
“起来吧,不是你。安排一下,去一趟大理寺大狱。”元辰摆摆手,眼睛落到贾雨村案的案卷上。
贾雨村在大牢内口吐莲花,高谈阔论,初见者都为此人的狂悖气质吸引,就连狱卒,也觉得按这位大人的谈吐,就是来这走个过场的事,外面保准早已有人在捞呢。
“大理寺少卿到。”随着一声清唱,一排黑衣人行动如风地站满了牢房过道,各个狱间的待审犯人都探出头来,心下忐忑着,这是要开审了吗?这位少卿怎么如此大的排场?是不是还有大人物要来?
红衣狱头率四个狱卒走过来,架起雨村就走。
“官翎一刻未摘,本官就是正四品,大理寺一日不划押,本官一日便无罪。狱头,你胆敢对四品官员元礼,是在这个地方呆够了,要高升了吗?”贾雨村面不改色,谈笑风声,语带风霜。
狱头识不了几个字,狱卒更是目不识丁,听到这唬人的话,吓得当即放了手,还涎着脸对背着手的贾雨村致歉。
谁知道那位上司,是来看这位,还是来审这位,按经验,还是别太得罪的好。
两个黑衣人上前,满身杀气地把狱头推开,径直上去,架起雨村便走。
看到他们黑面罩下露出的一双嗜血的眸子,贾雨村很识时务地闭了嘴巴,就是两只脚拉着地面划了一路,也很有城府地一声未吭。
一进屋,贾雨村眼皮一跳,以为到了地府。
满屋的黑衣人寒意凛然,手抚刀柄,目光齐唰唰地聚集到他身上,如万道冰柱打过来,贾雨村没来由地打了个冷颤,扑通一声跪倒在屋子中央,也没敢抬头看屋中正座上的大人,一连声地回道:
“大人,我全招,我全招。我还要举报同缭,争取立功。”
“说。”高座上的声音很轻,也很冷,带着上位者的矜骄。
“大人,下官知道那贾府的很多内幕,工部员外朗贾政是个糊涂蛋,他手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贪墨的,还有打着他的名号修陵时用次等材料的,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大人去查,下官都有和他的书信来往,愿做证据一并呈上。”
“打。”高座上的声音很不悦,也更冷了几分。
一个黑衣人上前,照着贾雨村的一边脸啪一掌打下去,肿胀效果比速效馒头还快,一边高一边低。
贾雨村以为上位大人对自己的举拱不够力度,也不敢用手捂脸,又磕了个头继续献媚道:“大人,还有一件更大的罪证,那贾府衔玉而生的公子,是个大祸害,下官亲眼所见,他抄了太上皇的一首诗,到处显摆是自己做的,您说,这不是明晃晃地僭越吗?大人,此人留不得,对皇室”
“打。”高座上的声音非常不悦,冷得好像带着冰碴子。
黑衣人上前,啪啪啪,两边的脸终于一样高了。
贾雨村终于懵了,他呆呆地抬起头,迷惑地看向高座。
年轻的大理寺少卿身穿黑衣,戴着黑金面具,白皙的下巴微微昂着,透着尊贵和锋利。
“贾大人,说说当初是怎么帮着贾赦逼死石呆子,强买古扇吧。”一暗卫上前,站到贾雨村面前。
贾雨村如获大赦,一把夺过旁边书计的笔和拱状,洋洋洒洒几千字,把当日经过写得详详细细,然后,讨好地看向高座。
大理寺少卿一声未吭,站起来径直走出去。
第二天,数日没有进展的贾雨村案件,很快解决,以利用公务之便欺压百姓,流放边关。
做为背后指使的大靠山,荣国公贾赦不思皇恩,心思歹毒,操纵官员,被撸爵,罚银一万两,无旨不得出府。
听完宣旨,荣国府一片愁云惨雾,贾赦在自己的东院喝得烂醉如泥,贾母在西院率一众媳妇姑娘哭得肝肠寸断,哭泣着自己的教子无方,生生在自己未入土前眼睁睁看着荣国公断送在自己手上。
贾政也多少风闻了雨村在牢内的攀咬,对友情的失望和官场的前途未赴,让他坐在空荡荡的书房里长吁短叹,颓废不已。
宝玉在听到消息后,喃喃地说了一句:“要来了。”后,胸口一闷,晕了过去,脸色惨白,滴水不进。
御书房内,元辰听着暗卫汇报,不可思议道:“病得厉害?这是最小的惩戒了,对那个贾赦,也就如隔衣骚痒吧?那位公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他说了什么?”
“他好像说了句‘要来了。’”
“要来了?什么要来了?”元辰皱着眉头,站起来,不安地踱着步。
“属下愚钝,但他自在书房和贾赦争论过后,便有点心如死灰的样子,听到旨意后,虽病得更厉害,但精神上却好像一幅解脱了的样子。”暗卫仔细回忆着细节,斟酌着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