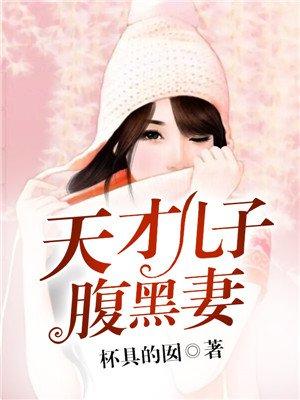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红楼第一梦指的是什么 > 第46章(第1页)
第46章(第1页)
宝玉看着贾母叹着气默认了,急了,走到贾赦面前拱手道:“救大老爷别把二姐姐嫁给那孙绍祖,他”
“不嫁给他,那嫁给谁,我没你家老爷的好命,可以做王爷的国丈。”贾赦斜眼瞅着他,嗤笑着他站着说话不腰疼。
“谁说二姐姐不能做王妃?明儿我便去求了北静王爷,让他给二姐姐相看一门好亲事。”宝玉急得口不择言。
“别介,宝二爷,我还丢不起那个脸,兄弟出面给姐姐找婆家,您老可真行。”贾赦朝宝玉埋汰地作着揖,嘴里拿话膈应着他。
王夫人有点恼,木着脸走上前,给贾赦行了礼,又转身斥自家儿子道:“行了,孽障,毕竟是大老爷的家事,你管不着的。”
宝玉急得眼泪都流下来,哽咽道:“老太太,太太,你们都不管,难道眼看着二姐姐被人打死吗?好,好,你们不管,我管,我这就去找北静王府,让林妹妹帮着想办法。”说完就跑了出去。
贾母急得站起来,朝屋内唯一的男人贾赦吼道:“还不快去拦住他。”
贾赦却冷笑一声,拂袖而去。
贾母忙又安排着王夫人坐了轿子跟上,这一个外男,直接去找表妹,算怎么回事?
北静王正和黛玉在花园里琴瑟和鸣,有下人通报宝玉要拜访王妃,有点惊讶问:“是你们听错了还是宝玉说错了?是拜访本王吧。”
黛玉拈着一朵芙蓉花,蹙着眉尖道:“不见。”
又一下人飞快来报:“贾家二夫人来拜访王妃。”
北静王释然道:“这才对了,快请夫人到内堂,本王去书房见宝玉。”
宝玉看到北静王腰里别着白玉箫走过来,知道他又在和黛玉和奏,沉着个脸拱手行礼道:“王爷,我林妹妹呢?”
水溶自小和他玩在一起,是知道他的性子的,虽长得是谪仙般的人物,但有时行事却乖张得很,当下也不恼,只戏谑地笑道:“我这里可没有什么林妹妹,只有静王妃。”
“是林妹妹不肯见我吧?”宝玉颓然地坐下,有点伤心。
“你家太太也来了,此刻正跟你林妹妹在内堂聊着。说吧,有什么事,值得你们一大早巴巴地赶来?”水溶抿了口茶,陶醉地摇摇头。
“跟王爷说有什么用,一个大老爷们,还能管姑娘家的婚事不成?”宝玉也端起茶,刚掀开盖,就闻到扑鼻的清香。
“怎么不成?你不是大老爷们?不也管上了吗?”水溶自婚后脾气不是一般地好,别说让他管一个姑娘家的婚事,此刻就是让他拿着绣花针绣个鸳鸯,他也乐滋滋地去挑战。
宝玉瞥了他一眼,破罐子破摔道:“跟您说也成,您听了,是笑话我还是瞧不上我,都成,只求你别到处嚷嚷就好。”
水溶挑挑眉,眼睛望过来,更加兴致勃勃,满脸的八卦与那张俊美的脸极不相称。
“我有个二姐姐,性子极软,只痴心棋艺,这两天大老爷要把她许经大同孙家,那怎么成,那个孙绍祖,是打女人的,我曾经做过梦,梦见他活活把二姐姐打死了,你说,我能看着二姐姐那样的面人儿,跳进火坑里而不管吗?而大老爷又是极推崇那孙绍祖是跟皇后娘娘是有亲的,我无法,只好来救林妹妹,让她帮着给二姐姐找个比孙家还好的婆家的。”宝玉义愤真鹰地说完,端起茶牛饮了一大口,嘭地放下。
水溶听得怔怔的,端着茶都忘了喝,直到对上宝玉那双怒气冲冲的眸子,才回过神来,恢复了一贯的云淡风轻,他拿着茶盖,轻轻扇着茶香,半晌,才慢条斯理地说:
“这事,还真不好办。不说,你只是做了个梦,不能当真的,就是你家大老爷的情况,是刚被撸了爵圈禁在家,这京城王公权贵圈里,哪个不是人精,谁会在这个时候娶一个随时会被连累的女儿为妻?再说那个孙绍祖,是忠顺王爷和太子面前的大红人,刚被派了和亲使的差事,爵至二品将军的,风头正盛,谁敢和他抢姻缘?”
宝玉闷闷地又喝了一大口茶,不甘心道:“世子哥哥自世袭了北静王爷后,也变世俗了,若是林妹妹,她必不会如此说。”
水溶轻笑出声,满脸春意:“你林妹妹?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如此说,但自大婚以来,她还没出过王府半步,京城的贵人圈子,她从来没参加过,要当媒婆,好像也无从下手啊,哈哈哈。”
宝玉郁闷地走出王府,碰上了早等在那里同样一脸郁闷的王夫人,娘俩无精打采地一起打道回府。
新月东升,宝玉对着棋盘,痴痴地发着呆,长长的睫毛瞅巴着,一串大泪滴落下,砸在一个白色的玉棋子上。
“石瑛为何哭泣?可出了什么事?”来讲学的朱先生和元辰站在他旁边一大会了,刚开始以为他在研究棋,就没出声打扰,直到看到少年泪水打湿了长长的睫毛,朱先生才才惊讶地出声问道。
宝玉抬头,匆忙擦干眼泪,朝朱先生行礼。
“你喜欢下棋?”元辰捏起那枚落上泪的棋子,温声问。
“我只是偶尔下一盘,要论下棋,谁也比不上我那个二姐姐的,她从六岁开始学棋,九年来痴心于此,超过师傅后,就天天自己左右手互相下,只不过是女孩儿,在后院里,没人知道罢了。”宝玉语气伤感,想到迎春的婚事无解,一口浊气又直直冲上胸口,堵得嗓子眼都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