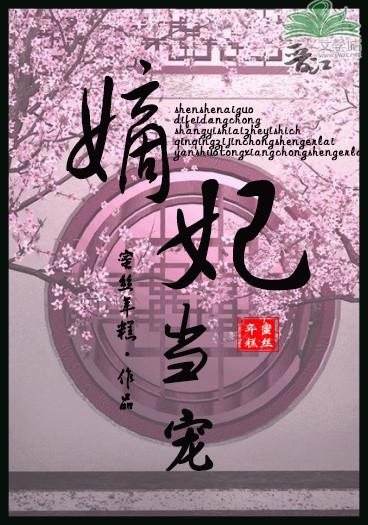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我诈死后再遇殉情未遂的魔尊/梦里长安躲 > 第80章(第1页)
第80章(第1页)
醒林垂着眼,冥顽不灵的模样,“说三道四又如何?我正好听个热闹”
虞上清当他这话是犯犟,训斥道。“胡闹!”
醒林道,“父亲,我没那般脆弱,况且,我总是要出门的。”
最后这话触动了虞上清,他本身便是个遇强更强的个性,天生浑不怕事,然他这儿子向来软弱惫懒,他一向当他需受呵护,没想到,儿子还有顶着众人的唇枪舌剑往外冲的一日。
他这是怎么了?虞上清不知道。但他知道,确实,儿子总要出门的。
最终,虞上清只能默许,醒林大为开怀,施了一礼,携了夏百友欲要离开,他走前,虞上清又叫住了他,将夏百友与众弟子先打发走,虞上清回过头,一双眼盯着醒林,既清且明,他淡淡地道:“那天地鼎的事,必会有人问你,你要先想好说辞。”
虞上清只说了这两句话,没容他多说,便道:“下午吧。”
他飘然而去,剩下醒林双手拱拳,独自僵硬了半晌。
父亲这话里话外的意思,那日自己对他所言天地鼎之事,他竟是不信的……
醒林头皮发麻,面无表情的从大殿出来,一路行来,待走到卧房时,麻痹消失,只感全然轻松。
他心中淡淡地道,就是要这样才好。
第二日,醒林一早跟着师弟们来到演武场,师弟们在作晨功,醒林抽了佩剑,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一招一式地演练了一遍本门入门剑法。
夏百友无事可做,在演武场旁溜达,看他半晌,看的直笑,他笑毕,抽了剑,用紫极观剑法陪他喂招,次品对次品,二人缠斗的难解难分,一上午很快便消耗过去,到了中午,二人饿极,与师弟们一处,捧着碗猛吃。吃饱后略作休息,下午又开始修炼。
一日下来,忙的没工夫胡思乱想,醒林觉得如此甚好。
想到不久后,要去玉房宫,人生中的日子与日子中间有了连接和目标,有了一丝丝希望,一丝丝盼头,他觉得更好了。
夏百友初来东山派,自然也不会日日困在岛上,偶有休息时,醒林带他上山下海,在四周走了个遍。
早几年,醒林太闲,将家门附近揣摩透了,附近所有好吃好玩的,按照远近优劣,心中早有个极为详细的单子。
他先带夏百友去逢霁楼,这是他在秋水镇第二个家,无论老板还是歌女都是他极熟悉的,他一来,立刻被引到自己惯用的独厅,醒林连酒水单子都不用瞧,直接让老板上自己爱吃的那几样,茶也是不消吩咐,老板自知他的口味。
夏百友在独厅外的栏杆上闲坐,望着眼前的内湖,望着亭台轩阁,啧啧称奇,对醒林称赞,“这奇工巧思,不像是小镇之物,比帝都的歌坊还清雅些。”
醒林淡淡一笑,自顾自喝茶,任由他四下游荡,细细观瞻。
从逢霁楼出来,醒林带他在小镇街边买吃食,夏百友方才在逢霁楼着实惊艳,见了这些路边小吃,却不甚感兴趣,他喜爱精致吃食。
醒林却不管他,他熟门熟路的沿街走来,挑着摊子买,买了糖葫芦,瓜子糖饼,牛肉干等物,买一样往夏百友怀里塞一样。
他走到炸鱼摊子前,要了半斤炸鱼,一回头,不见身边的夏百友。
这才发觉,夏百友站在远处朝他遥遥微笑。
夏百友捧着满怀小吃慢慢踱过来,醒林将炸鱼给他,夏百友笑着接过,没再多说什么。
在镇上消磨了许久,最后,醒林带他去了祈福山,时已傍晚,天空中一片彩霞,二人弃舟登岸,醒林携着他手,雀跃兴奋地讲着千年老树的传说故事,他喋喋说个没完,夏百友只微笑看他。
其实此处,着实无甚看头,不过是一座荒山,一棵老树,四周连一处亭台轩阁或名人墨宝也无,不过是这棵树在乡野有些传说故事,引得无知妇孺常来许愿。
夕阳西下,老树寒鸦,晚风徐来。
二人围着这一棵光秃秃地老树,站了许久,久到醒林终于将心中积蓄的话说完了。他望着平静的夏百友,自己也平静了下来。
夏百友笑着问他,“我虽然贸然前来,但醒林兄安排的招待有条有理,贴心周到,似是用心计划了许久一般,让我好生感动。”
醒林淡淡地望着他,在徐徐晚风中轻轻一晒。
满天红霞映着他二人,夏百友不说破,醒林也不说破。夏百友只当是醒林所费的心思皆是为他。他爽朗一笑,若无其事的一把搂住醒林,二人迎着夕阳向前去。
醒林被夏百友看透,倒并不慌张,只觉心下淡然,较往日还更轻松些,除了和夏百友在秋水镇游玩外,还带他打马去了县城。
他这次倒是没再买许多吃食,只带着夏百友逛了几个书摊,这正对夏百友的脾气,他在书摊旁一站便赖上了,手里捧着一本志怪话本,挪不动脚。醒林并不催他,眼光在众多书封上逡巡一圈,没一本他想看的。
夏百友端着五六本书,与书摊老板结了帐,醒林一本没挑着。
书摊老板一边乐呵呵的收钱,一边对醒林道,“听附近修士说有些新动静,你下次再来看看,许有新话本了!”
夏百友听了这没头没脑的两句话,疑惑道:“什么?”
醒林道:“好。”转身便走了。
他只得去追醒林,还未等他细问,醒林看到一家酒坊,回头问道:“沽些酒带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