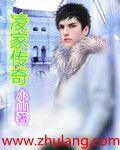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病弱黑莲花男主 > 第123章(第2页)
第123章(第2页)
沈陶陶睁大了一双杏眼,颤声道:“登……登徒子!”然后她赶紧把人往外一推,低头去看自己的衣服。
还好,自己的衣服倒还是好好的,就是不知道为何,身上多了一件宽大的鹤氅。氅上带着清冷的雪松香气,随着她的动作松松垮垮地坠下,一直散落到腰间,散落到宋珽的臂弯上。
沈陶陶这才发觉自己整个人都窝在宋珽的怀中,自己另一只手,似乎还紧紧地抓着宋珽的衣襟。而宋珽正低垂着眼,神情略有些复杂地深看着她。
她本就残存不多的酒意,被这一吓,也彻底的吓醒了。
昨夜里的记忆,也像是洪水一般,猛地出现在了脑海之中。
她想起了昨夜发生的一切。
她想起了自己醉酒后,把宋珽当成戏子,非要听他唱戏,还要听牡丹亭,听拜月亭,听汉宫秋,听窦娥冤。
宋珽说不会唱戏,自己便非要拉着他弹琴。
宋珽当真弹了一曲‘鸥鹭忘机’,自己还凑上去,与他说——‘小郎君人长得俊俏,琴弹得也好。’。
沈陶陶想起这句话来,一张净瓷似的小脸,立时红透了,烫得惊人。她恨不得如同鸟类将头埋进翅膀里一样,也将自己的脸埋进衣服里,再不见人了。
但她略一低头,差点撞上宋珽的胸膛。一愣之下,瞬间惊觉过来,自己好像就这样窝在他怀里,枕着他的肩膀睡了一整夜。
那一句登徒子,仿佛像是被夏风吹了回来,狠狠拍在她自己的脸上。
这怎么看,都是她才是登徒子,还顺道轻薄了宋珽。
沈陶陶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捂着红得几乎要滴血了的面孔,疾步便往府门外跑。
宋珽敛眉起身,一把握住了她的袖口:“你这样出去,明日燕京城里会怎么传?”
沈陶陶被他握住袖沿,被迫停下了步子,但是仍旧是捂着脸不肯回头看他,似乎窘迫得连话都说不来。
宋珽轻叹一声,取下自己的玉簪,为沈陶陶将散下长发束起,绾成一个简单的发髻。
这一绾,他才发觉,沈陶陶就连那小巧圆润的耳垂都已经红透了,似一枚深秋里熟透了的瓜果,引人采撷。
宋珽微微一窒,侧过脸去,淡声道:“我令钟义去备一辆没有辅国公府徽记的马车,送你回宫。”
沈陶陶仍旧捂着脸不说话,只是在原地站了良久,才小小地,微微地点了点头。
辰时未至,一辆马车便于昨日前来吊唁的马车们一道驶离了辅国公府,直至宫门前方才停下。
沈陶陶回到女官寓所的时候,江菱刚换好了女官服饰,正准备去尚籍司当值,见她进来了,便停住了步子,下意识地招呼道:“陶陶,昨日你让摊主捏的大黄,今日一早我帮你拿来了,就放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