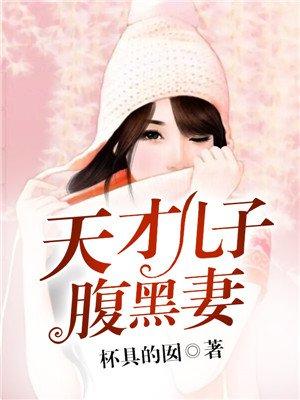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金鱼入沼简介 > 第55章(第1页)
第55章(第1页)
&esp;&esp;“你走去哪儿了,还没看见你。”
&esp;&esp;江稚茵实话实说:“好像走错了,我正打算直接打车回学校,但是位置有点偏,没人接单。”
&esp;&esp;明明听力有障碍,闻祈却还是很敏锐地发现她语气的不对劲:“你不舒服?”
&esp;&esp;“啊?”她又觉得嗓子发起干来,抬了抬头,“可能有点低血糖吧,我以前没这样过。”
&esp;&esp;“你把定位发给我,我现在过去应该很快,你原地歇一会儿,别继续往前。”
&esp;&esp;江稚茵干巴巴应了一声“好”。
&esp;&esp;她并没有走错得太离谱,闻祈十多分钟就到了,从出租车上走下来,江稚茵被他蹲下来的影子笼罩住。
&esp;&esp;以前不觉得,这还是金鱼
&esp;&esp;这句话说完以后,两人皆是沉默,江稚茵突然发觉自己的语言系统出现了宕机,像是一台年久失修的电视机不断飘着雪花的显示屏,接收到了错误而无法处理的信号。
&esp;&esp;邓林卓口中所说的那个词对于江稚茵来说一时无法理解,她似乎从未听说过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癖好,只是下意识地开口安慰着:“……也不能这么贬低自己。”
&esp;&esp;他并未表露出什么太明显的情绪,似乎也知道这只是她顺嘴说出的敷衍关心,唇角降下很细微的幅度,睫毛也往下坠,虚虚掩住眸中翻涌的郁色。
&esp;&esp;“你真的能接受?”邓林卓继续说,声音弱似呢喃,“其实并不是非常严重,现在已经好多了。”
&esp;&esp;已经难以记清第一次扎耳洞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可能是初三,也可能更早,应该就是他把江稚茵留下的风铃摔坏的那一天,下午对着洗手间缺了一角的斑驳镜面,直接用院子里捡的钢钉把耳垂穿透。
&esp;&esp;疼是很疼的,他一边用力让尖端刺穿他的皮肉,一边面不改色地咬紧后槽牙,漆黑的眼瞳在注视到自己耳垂的血洞渗出一滴滴鲜红色的血液时,就会感觉到心里的压抑稍微消失掉那么一些。
&esp;&esp;因为那时他不仅很恨江稚茵,也恨透了自己这一对无能的耳朵,所有人避他不及。
&esp;&esp;他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脏的东西,像放在水果店无人购买的生了虫洞的苹果,到最后只有溃烂到渗出酸水的下场。
&esp;&esp;没有做正确的消毒处理,耳朵很快就呈现溃烂的迹象,王奶奶下不了床,就托邻居带他去医院,在包扎好后,王奶奶一边流眼泪一边问他是不是被人欺负了,老人责怪自己无能,在他最需要依靠的年纪瘫了双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