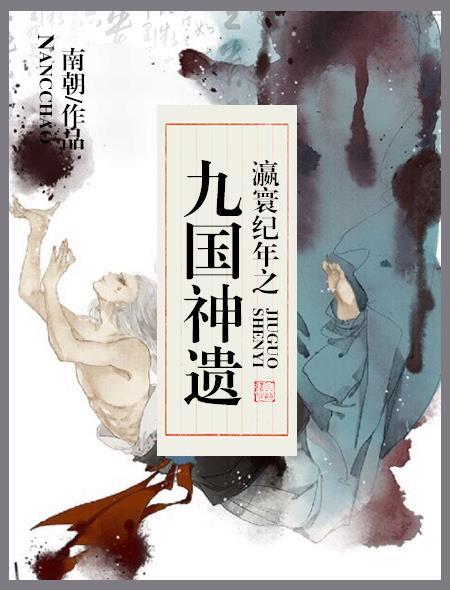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绯宇取名的寓意是什么 > 第8页(第1页)
第8页(第1页)
宋宇嘀咕道,“你叫我哥,你几岁?我都不知道我几岁。”“我十五。”苏朝晖答。宋宇放下碗,拿起苏朝晖脚踝上的锁链,捣鼓了半天,自言自语,“串子真他妈耽误事,让他教老子开锁,拖了他妈的半年。”他放下锁链,摇头,“小子,忍忍吧,我没办法。”见对方站起来像是要走,苏朝晖不知哪来的力气,撑着沉重的身躯,颤颤巍巍抓着宋宇的裤脚,道,“哥!那你留我一条活路,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我读过书,我是状元,我能挣钱。只要你不卖我。”他语无伦次,急的汗如雨下,“只要别卖我,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宋宇被这强烈的反应吓了一跳,他噎了半晌,往地上吐了口痰,“我能让你干什么?我他妈又不是掮客!”苏朝晖不死心,“那你让我干活,我能挣钱,也能吃苦。你相信我,给我个机会,我能挣到十倍卖我的钱,我挣不到,你怎么着我都行!”他一口气说完,心还在狂抖。这句话一出口,就已无法回头。苏朝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面对什么,但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而且要有手有脚,完完整整活下去,只有活下来,才有资格去想后面的事,所以哪怕只有一点点机会,也要搏一搏,绝不能在这里将一切画上句号。“还会谈判,真不错。”宋宇低下头看看表,又道,“那你老实点,我要出去了。章立文来了你不要惹他,他这个人脑子有问题!说翻脸就翻脸!”“好!好!”苏朝晖指着自己淤紫肿胀的脚踝,“我跑不掉!”宋宇离开后,苏朝晖的心又一次跌到谷底,但他强打着精神,好几次困得要昏睡过去,就咬破舌头来逼自己清醒。他不敢再睡,怕醒来又到了陌生的地方,又面对陌生的脸,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黑暗与罪恶。不知过了多久,安静的楼道上再次传来一阵滴滴嗒嗒的脚步声,苏朝晖睁开满是血丝的眼睛,艰难地伸头往上看。这些天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但凡听见脚步声,他对心会高高悬起。这种声音对他来讲就像是催命的号角,无论远近,都带着死亡的气息。他想起弄堂里的那只老狸猫,在吃掉老鼠之前,会把老鼠放在手里把玩很长时间,直到老鼠吓的心如死灰,放弃挣扎,才会心满意足地吃进嘴里。“以后这个人就跟我没关系,也别在侯爷那提我这茬。五万块不用给了。”“你还不知道我,”宋宇道,“我是蚌壳精投胎,军统都撬不开我的嘴。”苏朝晖听见那戏谑的谈话声,随即看见宋宇亲密地搭着章立文的肩,从楼梯走下来。:求生黑色的桑塔纳行驶在深夜的公路上。狭窄的后备箱里,苏朝晖像蜗牛般蜷缩着身体。长时间的卷曲让他周身的关节酸痛难忍,他不知道还要开多久,也不知道它将要去哪里,但此刻他只想把腿伸直,把头伸出去喘口气。这后备箱里奇颠无比,苏朝晖一把瘦骨快要散架,只能想些别的来转移注意力。刚才章立文和宋宇将自己带出地下室的时候,走得是另一扇门,门外是个僻静的小院,院里停着一辆黑色桑塔纳。他用余光去看,能看出那并不是游戏厅临近的主干道,而那家游戏厅显然也是他们的产业,是一份摆在台面上的营生。在淮陵,游戏厅行业受到严打,而在这个闻所未闻的小县城却开的风生水起,光是听都能听出人满为患。而宋宇说的那句“人贩子图财,亏本买卖不做”,苏朝晖是这么假设的,只要自己的价值大于被卖的价格,就不容易死,也就不容易被卖。这是初二思想政治课里的简答题——浅析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当然保命还不够,逃离才是目标。这里是城市,是文明社会,它的一切尚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而偏远山区,地下舞厅,黑工厂,那些蛮荒幽暗的无名角落,全是超出自己认知的可怕存在。未知,是比死亡更深的恐惧。就在苏朝晖快要窒息地晕厥过去时,终于呼吸到了最新鲜的空气。“能走吗?”宋宇打开后备箱,解开苏朝晖手脚上的胶带,拉了一把,“真能造,这么折腾都没发疯,造化不浅。”说完递了一瓶水给他。苏朝晖一瘸一拐从后备箱钻出来,好几次险些跌倒,还是努力稳住身型,亏得是晚上吃了些凉面和牙签肉,才不至于低血糖晕过去。走在前面的是章立文,他闷不吭声,唯独看苏朝晖的眼神还是带点微妙的愤恨,好像是煮熟的鸭子飞了,又像是到嘴的肥肉没能吃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