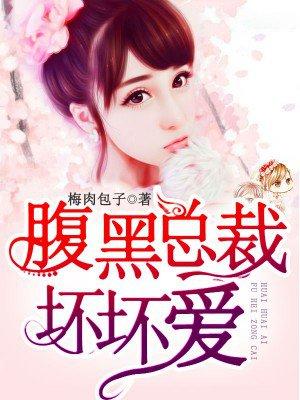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绯宇取名的寓意是什么 > 第105页(第1页)
第105页(第1页)
“没有。”苏朝晖缩回手,道,“我装的老实的很,他们没注意到我,没虐待我。我不哭不闹,听话,也不起眼,所以才有机会跑出来。”苏玲半信半疑,“你头上,脚上的伤,怎么回事?这不像是摔的。”苏朝晖道,“他们拿绳子捆的,勒出来的。”苏玲沉默了一会,又问,“过两天,等你伤都好透了,咱们去趟公安局,把情况说说。我就不让他们过来了,免得惹人说闲话。”“我当然记得,”苏朝晖点头,“是个团伙,在角县,而且底细不一般,上面是正儿八经的公司,有台面上的生意,养着底下的不法分子,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苏玲脸色发白,手指攥着茶杯,“你提醒我了,这几天我忙的发昏,老想着要跟说,话到嘴边又忘。”“什么事?”苏朝晖问。苏玲道,“院门口那栋,一楼的小吴,你记得吗?”见苏朝晖点头,她继续道,“立秋那头,小吴从外地回来,知道你的事情后,也跟我讲了一个事情。当年,你爸死的那晚,她被人跟踪过,那个人在她后面,差点就要把她拖走,她听见有人吼,‘干什么!干什么!滚一边去!’像是在骂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就跑了。她也跑了,:阴云华咏集团位于天启大道东段,黑色铝合金外墙沉稳大气,泛着低调的光泽。周一的早上,永远的繁忙。会议室内,一众集团高管围坐在椭圆型会议桌前,进行季末的总结会议。然而主席位上的侯镇林却靠在椅子里打瞌睡,与他一身笔挺的西装马甲格格不入。“在明年,我司预计达到营收入2000万,新增投资一个亿,产品净值增长57。”章立文的汇报声进到他耳中,这让他再次咀嚼起宋宇那条短信:小心章立文和陈国栋。那条短信之后,再也没有宋宇的任何消息。当晚李东发去新马要人,他们前脚刚到,后脚公安就到,索性没有参与斗殴,当地派出所问明情况后,就让他们走了。李东发带回两个消息,一,新马宾馆属于陈国栋的产业,这种组织打一枪换个地方,新马倒了,还有别的窝。据他那晚打听,当时被抓的人分两派,一派认为公司违法;一派为其辩解,更有甚者要回公司上班,双方差点又打起来。二,宋宇在里头呆过一阵,用的化名,一度险遭灭口,最后成功逃走。无奈宋宇联系不上,侯镇林的诸多猜测无法得到证实。那个手机号他查了,号主东北人,早就不用这个号了。虽然暗杀失利,但章立文这几天依旧神态自如:“为了衔接县政府资源,我建议我们出资份额要和县里达成互动,根据县里的诉求,具体协调…董事长,各位,汇报完毕,谢谢。”章立文看了侯镇林一眼,见他闭着眼,无动于衷。“咳。”今天到场的都是核心骨干,虽然见惯了侯镇林开会睡觉,但不知道他每次是真睡还是装睡,真睡假睡又分别是什么含义。会议室里落地听针,鸦雀无声。眼见众人齐刷刷看着自己,章立文只好走到侯镇林旁边,弯腰在他耳边轻声,“董事长,我汇报完了,请您总结。”“嗯?啊…”侯镇林如梦初醒,勉强地撑开一只眼,眼神迷蒙,声音含糊,“不好意思,睡着了,后面我没听清,麻烦你再汇报一遍。”章立文面不改色又念了一遍。念完之后,侯镇林带头鼓掌称赞,“非常好,非常好。”他直起身子,一手扶着脖子,一手按着桌面,语气懒散,“立文刚才说的,我表示绝对的同意。尤其是协调的问题。最近我深切地感受到,公司内部的沟通效率,有待提高,如果对于彼此的想法做不到充分的了解,那么展现在业务上的,就是由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潜在隐患。”他看了章立文一眼,继续道,“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也表示充分理解。“以往我们不开放沟通权限的原因,是考虑到各部门存有的业务隔离的情况,随着如今业务的增多、增广,我们的治理条款也会相应优化。我个人建议,要调整我们的信息传递机制,不严格按照层级,也不局限于书面授权。对于制度,大家一定要灵活看待,而不是我怎么说,制度怎么说,就生搬硬套去做。当初我们一同定了规矩,如今却困在自己定的规矩里,那叫作茧自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