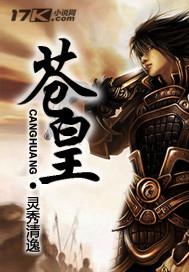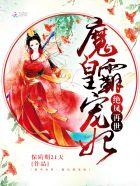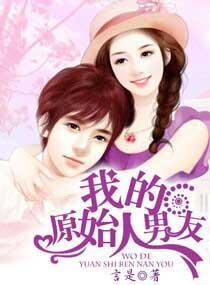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绯宇取名的寓意是什么 > 第138页(第1页)
第138页(第1页)
刚过五岔路口,他看见前方公用电话亭旁,站着一个矮小的女人。苏朝晖停下脚步,目光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流,直逼那道身影。那女人侧着身,正在和另一个男人交谈。男人背对着马路,看不清面孔,只能通过他偶尔的警惕地顾盼,看见他黝黑干瘦的面孔。苏朝晖心一沉,直觉告诉他,这就是那晚在夜总会门口卖玉米的女人。他将手放进口袋,抽出那张一直揣在身上的通缉令。实际上,以苏朝晖过目不忘的能力,通缉令上的脸,他记得住;夜总会门口的脸,他也记得住,但两张脸放在一起,一个圆润臃肿,一个憔悴干瘦,乍看之下截然相反,很难将二者联系到一起。看来通缉犯的日子确实不好过。虽然直觉可以确定,但那向来习惯求实和考证的精神让他不敢下结论,于是决定跟上去,试图看清她的脸。夜幕很合时宜地降临。女人和男人交谈一阵后,各自往不同的方向走去。苏朝晖跟着女方,始终保持着三十米左右的距离。路过一处服装店后,女人像是察觉什么一般,忽然回头了。苏朝晖若无其事地移开眼神。现在他装傻的本领,早在角县和光明练得炉火纯青。就是她。潘秀英。现在他可以这么确定。即使容貌大变,但在她回头的瞬间,那眼中蛇一般的冷漠和贪婪,与通缉令上的画像几无差别。苏朝晖揣在口袋里的手开始冒汗。他不得不感叹画师的炉火纯青。看似草草几笔,实际上画出了精髓:那种对生命的漠视,对法律的蔑视,对真善美的无视而造就的阴狠眼神,只有长期与罪恶交集的公安才能洞穿。“集贸市场”四个大字在夜色下逐渐模糊。女人往菜市方向去了。这里的交通一塌糊涂,苏朝晖绕过车流,跟的很艰难,三轮和摩托排着蛇一般的长队,行人在其中穿梭,夹杂着此起彼伏的鸣笛与吵嚷。但苏朝晖并不觉得嘈杂,他生来就在闹市,早已习惯嘈杂。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确定这个女人的落脚点,然后报给公安。在角县的经历让他明白,这些人都是打一枪换个地方,他们眼线众多,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甚至可以说黑白通吃,盲目报警只会打草惊蛇。进了菜市之后,潘秀英越走越快,在一处肉铺门口停了下来。苏朝晖也放慢了脚步,他在卖西红柿和黄瓜的摊前蹲下身,拿起一个西红柿,看着那家肉铺。眨眼之间,潘秀英一个转身,拐进了肉铺旁的胡同,苏朝晖急忙放下西红柿追去,却已不见任何人影。他茫然地站在这条死胡同前,看着里面棺材般的大木箱和破损的箩筐。“让开让开!别挡事!”随着一声斥责,苏朝晖被人大力一堆,撞到了胡同边的宣传展板上。男人端着一锅沸腾的肉汤,掠过苏朝晖进了肉铺。苏朝晖揉揉撞疼的肩膀,他转过身准备离开,恰好看见一张寻人启事。这是集市里常见的宣传墙,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广告,由于平时没人打理,很多纸张破烂不堪,沾满了雨水和油污。正中央这张告示像是新贴的,纸张很新,上面“寻人启事”四个大字和孩子的照片尤为显眼。苏朝晖走上前,认真地看着上面的内容:失踪的男孩只有九岁,半年前,在这个集市走失,至今没有找到。告示的后半部分被一张广告挡住,苏朝晖顺手将广告撕开,将告示完整地露出来。一撕之下,他惊讶地发现,这广告单后面还有另一张寻人启事。失踪男孩4岁,两年前在这个集市失踪。这一刻,苏朝晖后心开始发麻,他试探着,再撕下一张就近的广告纸——果不其然,后面又是一张寻人启事。苏朝晖撒开了手,一张一张地开始撕,彩色的纸屑很快就落得满地都是。天彻底黑了。身后的路灯亮了起来,恰好照在这面广告墙上。苏朝晖不知道撕了多久,直到脚下彩纸随风乱飞,直到再没什么可撕。撕完之后,他开始数。借着幽光,他辨认着寻人启事上的脸,开始一张脸一张脸地数。数着数着,他越来越冷,他胆战心惊,如坠冰窖!如此小小的,不起眼的一面墙上,竟密密麻麻地贴了将近三十个寻人启事!他们都是10岁以下的幼儿,且全都失踪在这个集贸市场里!苏朝晖像溺水的人刚从水中浮出一样。他深吸了一口气,倒退几步靠在路灯旁,震惊又茫然地愣在那里。一只被剥了皮的牛蛙缓慢地从他脚上爬过,挣扎几下后翻过肚皮,再也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