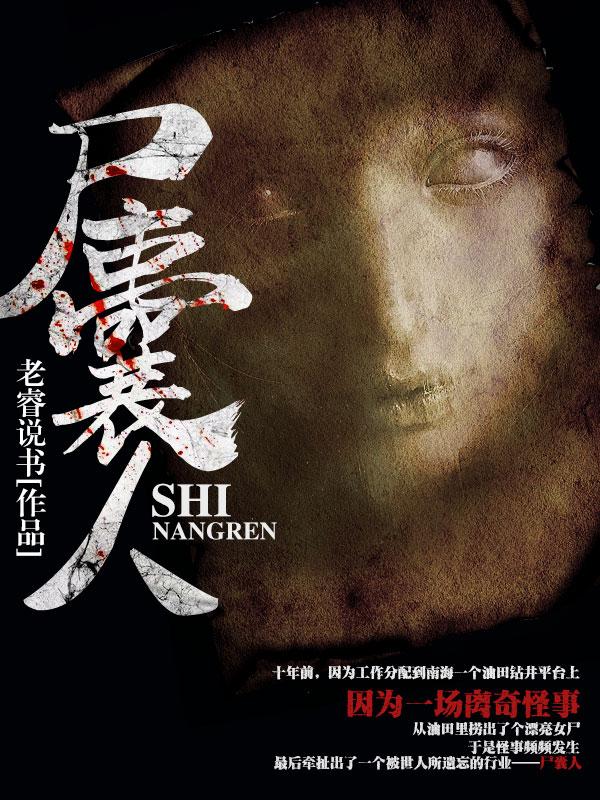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谁与渡山河和谐在哪里 > 第309章(第1页)
第309章(第1页)
有些事情他不愿意明说,就是给彼此留着体面,他是真的没有想到,下了朝还有人要在他眼前蹦跶讨嫌!百官阶下齐声相胁,陆数是真当他这个主君不介意嚒?!
陆数抬头,眼神有了几分郑重:“在天灾或是政局动荡的时候,本来人心浮动,风言风语迭起,这出于恐惧焦虑,也不能说是全部因为臣子们的居心叵测……倒是殿下,您今日心中已起了成见,来日同朝议事,这岂不是要推拒百官与您为敌?”
辛鸾的眉梢轻轻一跳,这一次,没有做声。
“殿下敏情善察,今晨那个情况,您的确算得稳,做得到,以有心,压无心,之后又有邹将军捷报,一胜压住百丑。可您想必也知道,很多人嘴上虽不说,心里却是不服的,您今日捏住别人的小辫子赢得今日这一场,难保来日别人不会寻您的短处。”
辛鸾眸光忽地一利,刀一样射向陆数——
陆数毫不畏怯:“阴谋之君,才有阴谋之臣,您的心就是偏的,又怎么能怪朝臣有失公允?以暴制暴,往往不能解决问题,这样的冲突多了,能伤害对方,也能伤害自己。您尚且未握独断乾纲之权柄,就不怕众人真有一日联合起来,把局面闹到不可收拾?”
辛鸾的脸色越发不好看了,坐在榻上缓缓直起身来,一字一句,“陆数,你要给孤看的本事,就只有危言耸听嚒?”
他用人头数来压他?他将来会面对什么,他掂量得清楚,还不用这么个没轻没重的官吏来提醒:事关邹吾性命,哪怕让他从来一遍,他还是会这么做。
“这不是危言耸听。”
陆数的桃花眼,也流出几分凌厉森寒:“殿下您今日相强百官是事实,言之凿凿,立论煌煌,看似占理,其实谁都看得出您意欲何为,可一个之前未发过一条政令、说过一句准话的小太子,之前一直默然不语,因为事关自己亲信了,就忽然在家国大事前指手画脚,您要臣工,又如何能服?”
辛鸾登时坐不住,掀开被褥,趿着鞋直接气势汹汹站了起来——
陆数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会觉得小太子会打他,忽地一个避让,抱住自己珍贵的头脸,“殿下可不能动手啊,臣好歹是有品阶的臣子!您也是个斯文人……”
辛鸾被他气得胸有激雷,站在陆数的面前喘了好几口气,最后还是大步绕过陆数,几步走到窗下,面朝窗外,一语不发地急剧思索。
陆数在胳臂的缝隙中扭身看着辛鸾的反应,见状,他眉梢轻挑,知道自己赌对了。
·
“五月九日是祭神大典,在那之前,咱们的功臣也回来了,为免劳民伤财,有功之臣的封赏嘉奖就在大典之后一道行了吧,将南境的大捷上高于天,也不必分着举办两次了。”
向繇:“是。”
辛鸾:“这次祭典就祭坛就不要设在钧台东侧的祈神台了,设在中山城。君民同乐的喜事,不要只是南境公卿权臣来观礼。”
这倒是出人意料了。申不亥解释道,“可南境自天衍开国以来,都是在祈神台祭祀奉神的。”
“历来?”
辛鸾心平气和地反问,“南境之前也像今年一般有高辛氏驾临?”
申不亥:“……”
“时移世易啦右相,”辛鸾轻轻地笑了下,“您就没想过祈神台为什么在巨灵宫东殿的钧台宫的最东侧?面朝东方,这不就是要遥拜高辛氏的三足金乌,遥拜真正的帝王之气嚒?”
这个解释,有谁敢说不是?
申不亥砸了砸嘴,只能哑口。
向繇缓缓插口:“殿下说得是,远的不说,南境朝廷这十几余年的确是供奉三足金乌与东皇。”
向繇别有用心加了“朝廷”两个字,辛鸾只当没注意这个词,顺着话道:“现高辛氏正统血脉就寓居渝都,那也不必再起用东侧的祈神台了,就在中山城最大的万人场搭祭台、燃祭火,可开放让百姓前来观礼。”
天衍朝每年的祭祀仪典从来极为庄重,为表对上天与鸟图腾的赤城之心和极致敬意,往往由身份贵重之人上台领舞祝祷。
辛鸾:“这次献舞的也不用选别人,我亲自领舞祝祷,右相你回去找负责礼乐和歌舞的官员来和我谈具体的。”
申不亥长大了嘴。
向繇睁大了眼睛:“啊?这……”
“敬神的仪典事关帝王的气数,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和象征,前几年领舞者不是天子,全是因先帝日理万机少有闲暇,才逐渐演化成择一身份高贵的世家子弟领舞。新朝该有新气象,式明王度,正本清源,两位丞相按我说的做就是了。”
辛鸾这局棋下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乍一看都没有什么问题,结果一步步把他们带沟里了,直到现在,略窥全貌向繇才隐约听明白他的全盘意图。
祭祀乃家国大事,可这些年渝都信奉蛇图腾居多,向繇暗中推波助澜,连续几年的鸟图腾祭祀都极为含糊敷衍。辛鸾先是要把大捷封赏定在祭神大典上,紧接着又转移祭神场所,要百姓观礼,最后又要亲自下场,这几招下去,所有人都会忽然意识到,蛇祭不过是民间的淫祭,只有他高辛氏的鸟图腾才是正统,才能上大雅之堂。
辛鸾初来乍到的时候嘴上说着并不插手干预民间的风俗祭祀,现在却忽然动了这个心思,向繇心中有鬼,想着是不是那天地宫的事情,并没有瞒过去?他将地宫方位摆成巨蛇受万人供奉,这些年又潜心经营民间蛇庙,就为了安哥儿能身体康健,多受些香火……这个小太子,是不是终究起了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