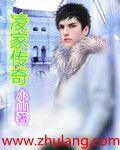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和平精英免费 > 第二十一章 老太太(第1页)
第二十一章 老太太(第1页)
第二天一大早,一间简单温馨的卧室内,一个女人正睡得香甜,男人的?33??音从房间外头传来。
“老婆,起床吃早饭了,今天我决定请假在家好好照顾你。”
女人呢喃一声,舒服的伸了个懒腰,如同往常一样熟练的掀开被子,起床,洗漱,再趿拉趿拉地走到厨房,全身甚至都不需要睁开眼睛。
“你刚才和我说什么?请假,干什么请假?”女人迷糊地说道。
男人一边再桌子上摆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半开玩笑地说道:“我们才刚结婚不久我就抛下得了重感冒的你独自去上班,要传出去你爸非得打死我不可,所以我就想着今天请假。。。。。。”说到后面男人住了嘴,侧过头惊疑地盯着老婆,有点不敢相信地问道:“你感冒好了?”
女人也一下子呆住了,深呼吸几下,鼻子不堵了,使劲干咳几下,喉咙也不干燥难受了,最后憨憨地晃了两下脑袋,脑袋也不晕不沉了。
“好像,真的好了?”女人迟疑地说道。
“哈哈,太好了。”男人高兴的一下冲上来抱起女人转了个圈,笑道:“这下我可以放心的去上班啦。”
女人以快如闪电般的速度捏住男人腰间的软肉,恶狠狠地说道:“你就这么不想在家照顾我?”
男人感受着腰间传来的阵阵刺痛,连连讨饶:“老婆,错了,我错了,我今天请假在家陪你还不行嘛。”
女人一瞪眼,更生气了:“谁允许你请假了,你不去上班谁赚钱养我?”
“。。。。。。”
早饭过后,男人遵照女人的吩咐乖乖去赚钱,女人昨天本来已经请了假做好和感冒长期抗争的准备,尽管感冒已经痊愈但她也没有立马去上班的打算。
女人嘛,就该对自己好一点,赚钱养家这种体力活就交给男人吧,自己负责貌美如花就好。
女人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昨天花“高价”买的小盒子,她可不认为自己昨天得的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感冒,感冒有多严重她自己再清楚不过,但是在一夜之间竟然神乎其技的痊愈,难道。。。。。。她心中有个大胆的猜测又不敢去完全相信。
她的职业注定会让她知晓许多杂七杂八的消息,据她所知,从来没出现过对于感冒速效的灵丹妙药,也不是没有过重感冒一夜之间好了大半的例子,头脑清醒后恢复理性的她不会轻易去相信自己的猜测,她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这件事。
当小桔盯着面前这位漂亮的女人时,脸上满满的愕然,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一大早就等着来买在她眼中只有傻子才会买的药。
女人轻笑一声,感觉眼前这位喜欢走神的小姑娘很有意思,升起了逗逗她的想法,从包里拿出口罩戴上,戏谑地说道:“怎么,不认识了?”
小桔更吃惊了,竟然是昨天买过药的女人,她的小脑袋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接二连三的当傻子。
“小姑娘,别发呆了,昨天那个药再给我拿两盒。”
“哦,好的。”
几分钟后,女人拿着几盒包装精致的888感冒丸离开,心里思量着哪里找得到得了感冒的人。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不要说一手把蔡仁堂打入谷底的几家药店老板,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关注到蔡仁堂上架的新药但隔天早上他们还是都收到了消息。
洪福堂的老板收到消息如同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般在办公室哈哈大笑:“888感冒丸?蔡仁国这是气不过三九集团存心想恶心他们啊,哈哈哈。”在他看来一定是蔡仁国被逼得狗急跳墙才会做出这种类似小丑的行为。
其他几家药店老板也都抱着相似的看法,认为蔡仁国不过是翻不了身,临死也想往他们身上泼一桶脏水试图恶心他们,但这在他们看来就是个笑话。
他们现在满心考虑的是蔡仁堂倒下后如何去分空出来的一大块蛋糕,在蔡仁堂还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江城医药界除了洪福堂就没有第二家药店可以和蔡仁堂媲美,一旦蔡仁堂在他们联手加上三九集团的打压之下倒下,那空出来的市场份额可是诱人的紧,如此巨大的诱惑摆在眼前哪里还顾得上如一滩死水的蔡仁堂,暗流早就在桌面下开始涌动了。
几天过去,888感冒丸的销量并没有呈现一个爆炸性的上升,每天仍以几盒,十几盒的销量缓慢售出,然而丁白那里的药丸却仍不间断的产出,经过第一天的乌龙事件,蔡大锤送过去一个不大不小方便保存药材的柜子,所以丁白不需要一次性把药材全部用完,大概以每天2000多颗的速度持续产出,他也没有多过问其他方面,只是每天早上按照惯例把2000多颗药丸给过来拿货的人员就安心的当一个甩手掌柜。
这天,丁白起床后习惯的开始了他的发呆日常,几天来除了第一次交货给蔡大锤时完成的委托,他的万能和平屋就再也没有开张了,左右无聊的他索性每天跑到边上几家店铺聊天,倒是和附近老板的关系都搞得不错,边上几家店的老板也对这个店名古怪,开店时间随意,关门时间更随意的年轻店铺老板感到好奇,他们私下里一直把丁白当成是某位闲的蛋疼的富二代,毕竟他们经常听说富二代这一群体稀奇古怪的各种事迹。
晃晃悠悠地从隔壁渔具店出来,相谈甚欢的俩人还信誓旦旦地约好有空一定一起去钓鱼。回到万能和平屋的丁白从怎么喝都喝不完的果汁机里倒了杯果汁悠闲地躺在沙发上小憩,如果不算任务列表里一分一秒减少的时间,丁白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真的是比神仙还舒服,毕竟神仙也是要干活的。
闭目养神的丁白没有注意到他的门口忽然冒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用褶皱的手架着一副老花眼镜努力地瞧着丁白贴在玻璃门上一直未曾撕下的那张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