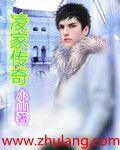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女配也是重生的 > 第89章 她的身孕(第1页)
第89章 她的身孕(第1页)
萧眠觉得赵非蕴福大命大。
流放路上那般的艰苦他都熬过来了,怎会栽倒在小小的瘟疫之上,萧眠一路上都这样安慰自己,只是等到不顾阻拦看见白着脸躺在那儿的赵非蕴的时候。
脑袋里还是嗡的一下。
什么念头都没了。
只剩下要是眼前人死了怎么办?
此念头一旦冒出来,压都压不回去。
萧眠用力摇头,坐到了旁边,眼泪到底是掉下来,打湿了口鼻处的布巾,她沉默片刻,让老邹出去,拧了下帕子,替赵非蕴擦着手。
絮絮叨叨。
“你说你啊,当初面对几个劫匪都说不关你的事,如今倒是厉害了,为了百姓竟然能命都要送掉。”
“你说你的父王母妃兄长知道了,是不是会以你为荣?”
萧眠动作很轻柔,赵非蕴无半点反应,只是张嘴轻轻呓语,语气太轻,她根本没有听清楚。
不过不要紧,萧眠也不在乎这个,继续与她说话,如同情人间的轻声细语,“我想定然是会的,谁不知道长安城的翩翩佳公子,赵非蕴,可是荣王府的一颗明珠。”
她笑了笑。
这话不是自己夸大。
荣王一生征战沙场,与王妃恩爱有加,一生育有三子。
长子自十岁起便与其父身披铠甲,从最底层小兵做起,一路建功立业,做到偏将,是人人敬重羡慕的年少将军。
次子赵非蕴,不爱兵法爱诗书,五岁师从当朝儒学大家董五子,八岁口出成章,十岁成赋,十二岁跟着荣王外出历练,出计剿匪,解救了百姓,仁厚的贵公子名声响彻天下。
深得先帝喜爱与夸赞。
先帝没有成年可担当大任的子嗣,那段时间,宫中传闻要从皇家宗嗣之中选出嗣子,作为下一任新帝。
消息一出,虽然没有明确,陈钦那些人也未曾进京,但长安城几乎人人都认为赵非蕴将是无可厚非的新帝人选。
哪知道。。。。。。
造化弄人。
赵非蕴虽然表面淡定,但萧眠知道他平静的表面下却埋藏着巨大的火焰,只等待着一个出口爆发。
父母之仇,荣王府几百口人所流的鲜血,都无时无刻不在他心中浮现。
萧眠想,要不是因为赵非蕴内心本善,还存着天下百姓,或许也管不了这些人,更不会沦落到如今躺在这里的地步。
老邹端来一碗药,滚烫的烟气扑到脸上,萧眠竟然有片刻恍惚,舀了一勺吹凉递到赵非蕴嘴边,“喝药吧。”
“喝完你就好了。”
话虽如此,可是赵非蕴却丝毫不配合,牙关紧闭,墨黑的汤药从嘴角流出来,将脑袋下藏青的枕巾打湿一片。
“怎么会,两个时辰前还能喂进去!”老邹见此情景,慌了。
他没想到,县令的病情竟然加重了,要是连药都喝不下,还谈什么恢复痊愈。
“大人,您要坚持呢,只有喝了药才能好。”老邹几乎要跪下了,说句实话,他的心跳的飞快,腿脚不自觉发软。
口中念念有词,此刻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了。
萧眠没有说话,只是目光变得幽深,又喂了一勺,还是一样的结果。
她默了默。
忽然将药碗递给老邹。
老邹愣愣地接过,还不明白萧眠到底要做什么,他张大嘴巴,就看见萧眠左手捏住大人的下巴,迫使他的嘴巴打开,右手拿过碗,就往他的嘴巴里慢慢灌进去。
虽然流了一小半,但好歹有一大半喝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