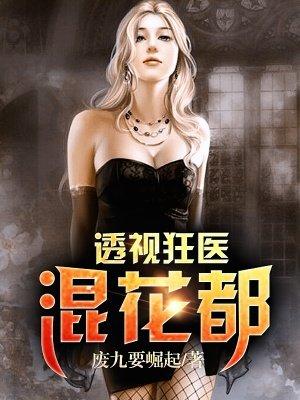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阴缘 剧透 > 第263页(第1页)
第263页(第1页)
所以没几个人注意到,谢夫人居然在这般情形下仓皇扑进了偏厅,疯了一样去拽那已经烧了一半的绸缎。“啪。”头顶上的房梁脆响了一声。这样吵的环境中,谢夫人居然还清晰地听见了这一声。她抬头——眼珠中火光像是一条,随即陡然扩大。“咚!”房梁断开砸下一半,从肩膀到腰腹,斜轧开一大条口子,肉焦味一下子充斥了谢夫人的鼻腔——同一时刻,小佛堂中被谢家人供奉了十几年的陶罐突然疯狂抖动起来,罐底“咯嗒咯嗒”地撞击木桌。某一刻,它终于挪到了桌子边缘狠狠砸向了地面。灰白色的骨骼残渣和不知道来自哪里的黄土散了一地。而后,小佛堂中陷入了安静。但谢夫人房间中,一直呆呆木木的小男孩抬起了头。他喉咙里发出兽类一样尖细的叫声,四肢着地,快速朝门外爬去。【逃……逃……】就算这个活人的躯体盛不了它多久,就算不要骨殖,它也得逃出这里……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黑暗中有东西笑了起来,它也像是兽类那样趴俯下来,好整以暇地等在黑暗中。在这只狐鬼的身躯到来时,压住了他的头。黑暗中活人的身体不断挣扎,但头上的重力越来越重,头骨开始开裂,骨骼断裂处刺开皮肉,脑浆和血液一起流下来,眼球挤出——压烂。这具身体停止了挣扎。祂顿了会,似乎叹了口气。狐鬼逃走了。【可惜……嘻嘻……可惜……】宋时清蜷缩在床上,沉浸在一个充满血色的噩梦中,他无意识抱住被子,揭开往里面躲,仿佛这样就能逃脱某种既定的结局一样。他叫谢司珩哥哥,谢司珩也真的将他当弟弟看待。那些隐秘的,在七百多日的相处中探出一点点嫩芽的情愫,就该被掐断。谢司珩不说,宋时清不懂。它本该藏在时间里,藏在生与死的隔阂之间。或许多年以后,宋时清对另一个人产生同样感情的时候,会突然想起年少时的过往。谢司珩本该安安静静地待在他的记忆里。【够了。】宋时清听见了自己细弱的哭声。【够了……谢司珩……够了……】剩下的……剩下的他不想知道了。谢司珩抓住了他的手指,放在唇边亲了亲。谢司珩(看着缩在床角的宋时清)(委屈):又不是我要走强制路线的宋时清:……(钻进被子里)火,到处都是火。滚烫的空气触碰宋时清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带来一阵烧灼感。宋时清不解地朝前走了几步,而后就被远处的景象惊住了。浓烟后面,谢夫人仰面躺在断裂的横梁下疯狂挣扎,她两只手竭力将沉重的横梁往上推,神情痛苦狰狞,无声哀嚎着。宋时清看着她大张着嘴,里面躺着可怖的血红舌头。她瞪着宋时清,神情既怨毒又带着不易察觉的哀求。【救我……快救我……】宋时清缓缓朝后退了一步,同一刻,另一人与他擦身而过,恐惧地跑向了谢夫人。那是伺候谢夫人的婆子。大概是护主心切,亦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婆子猛推横梁,试图将横梁推开。谢夫人浑身一震,张合嘴唇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婆子喊话。但燃烧的噼啪声和人们仓皇的叫喊完全将她的声音淹没。大量血液从女人的嘴里涌了出来,骨骼断裂的声响钻进了宋时清的耳朵里。——【时清,你猜她会不会死?】宋时清被耳边的声音吓得一颤,脑中空白之下,他全身只有眼珠能够转动。于是他垂眼看向身侧,入目的先是一只搭在他肩膀上的苍白人手,往上,他看见了身侧人手腕上的尸斑。大概是察觉到了宋时清盯在它手上的目光,谢司珩弯腰,将头慢腾腾地压了下来,一张苍白的,带着恶意微笑的脸就这么抵在了宋时清的鼻尖前。活人绝对没有这么高,骨头也无法这样弯折。宋时清呆呆地看着眼前长着谢司珩脸的东西,它也注视着他,笑嘻嘻地开口——【哥哥问你话呢,你猜她会不会死?】宋时清唰一下睁开了眼睛。他剧烈呼吸,心跳得极快,好半晌才一点一点从噩梦中挣脱了出来。回想梦中身形怪异诡谲的谢司珩,宋时清缓缓坐起来抱着被子发了会呆。我怎么会梦到那个样子的哥哥?这一会的功夫,身上的汗凉了,黏着头发贴在脸侧颈侧,痒痒的不太舒服,宋时清顺手理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