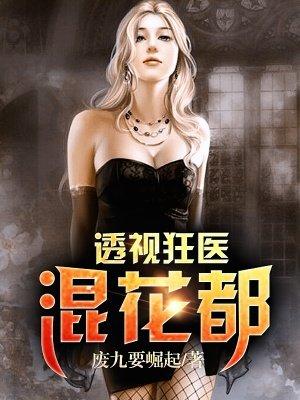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被渣后被绿茶影帝撬走我 > 第170章(第1页)
第170章(第1页)
被大家注视的白袍人冷漠的目光穿过虚空,虚虚落在邱秋身旁的南寻殷身上。
“是你。”如碎玉般清脆冷冽。
南寻殷气度卓然的立在一处,微微一笑道:“顾兄,好久不见。”
话音未落,便见白袍人眉梢一挑,抬掌朝他劈去。
南寻殷瞳孔微缩,连连后退,弯腰躲过。白袍人冷漠的一扬眉,另一掌就接着劈来,眼看掌风将要触及身体,南寻殷侧身去接,做好了生受一掌的准备。
这时一把弯刀滑过,挡住掌风。
大当家不知何时已到南寻殷身侧,他手举弯刀,脸上还残留着对白袍人的惊惧,低声祈求道:“前辈,如今大灾当前,有什么恩怨可否以后再说?”
白袍人眉眼未动,手掌如灵蛇般饶过大当家,狠狠的拍在南寻殷身上。
南寻殷砰的一声被打得飞出数米,哇的一声吐了口血。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不过片刻,便见着南寻殷躺在地上。
邱秋上前扶住他,擦了擦他嘴角的血道:“还好吗?”
南寻殷轻咳几声,将涌上嘴巴的气血噎了噎,轻声道:“无碍。”
大当家未曾想这白袍人掌法如此厉害,他暗暗叫苦,圣使关系到他们一族的存亡,若是圣使出事,他们非但不能找到解除诅咒的法子,或许还会开罪大雪山。但这白袍人看着也不是好相与的,能一刀劈散雪峰的,整个三域不出几个,这恐怕得宗师修为才行。
他暗中戒备着白袍人,亦去到南寻殷身边:“圣使,您没事吧?”
此话一出,南寻殷扶着邱秋的手一顿,暗道一声:“糟了”
果然,本收了掌,负手立在一旁的白袍人听到这个称呼,眉梢一扬,低声玩味道:“圣使?”
大当家向前几步横档在南寻殷面前,温声道:“前辈,这位是大雪山的圣使,前辈就算武功高绝,想必也不愿在这雪原中与大雪山为敌吧。”
话音一落,白袍人身边胖胖的中年人先笑出声,目光在几人身上转了一圈,冷喝道:“大胆狂徒,竟敢假冒雪山圣使,你可知站在你面前之人是谁?”
大当家被喝的一愣,面上迟疑之色闪过,方呐呐道:“圣使可是有银月牌作证。”
“咦?”胖胖的白袍中年人面上流露出几分惊讶之色,他目光凝视南寻殷:“他说的可是真的?你从哪里得来的银月牌?”
南寻殷却未搭话,他在邱秋的搀扶下站起身子,微微苦笑道:“顾兄,我们好歹认识一场,你这份见面礼未免太重了。”
顾白原眉眼未动,一派冷漠道:“南寻殷,七年前你潜入我大雪山,盗取心法,如今还拿着我大雪山令牌招摇撞骗,你入了三域,我鞭长莫及,如今你自己送上门来,就别怪我取你性命。”
白胖胖的中年人恍然大悟,随即咬牙切齿道:“原来你就是七年前那个小贼!”
这一番变故,大当家面色铁青,目光即骇人又复杂,蝎子与虎头凶狠的瞪了瞪南寻殷。
邱秋却听得目瞪口呆,她就说南寻殷怎么突然就收服了这帮蛮匪,个中缘由竟然是这样。不得不佩服他的同时,心中又很好奇南寻殷与大雪山的恩怨。这人可真是神通广大,好似哪里他都能插一脚是的。
被揭穿身份的南寻殷,半点不惊慌。他面上含着风轻云淡的笑容,一派从容自若的风度。便是身上的粗布麻衣也掩饰不了周身的沉稳贵气,这是久居上位的人才有的处变不惊,淡定从容。
他笑了笑:“顾兄此言差矣,当初贵师弟与我打赌,我若能不惊动任何机关潜入贵地藏书阁,其中心法便可任选一本带走。愿赌就要服输,那本心法是我堂堂正正赢走的,何来盗取的说法?”
顾白原的师弟云亦安是个痴迷机关的天才,当初南寻殷急需心大雪山心法,知晓云亦安这么个人以后,便设了个陷进引他入瓮,又故意以机关之术激他。天才嘛,总是比寻常人自信,南寻殷何尝不是,两人便相约与机关作斗,一赌输赢。
大雪山机关最多最灵巧之处便是大雪山的藏书阁,里面的机关又十之八九出自云亦安之手,可惜结果是他略胜一筹赢了云亦安,带走了心法秘籍。
顾白原眉宇间闪过几分凛冽,手扶腰间弯刀,寒气森森的道:“我雪山弟子私自拿心法作为赌注,违反雪山禁令,我已亲自惩戒,而你,外人偷学心法者当诛。”
这般杀气腾腾的话,南寻殷并未有半分惧怕,他叹道:“顾兄,我与你在雪山相交两月,互为知己,你非要这般不近人情?”
顾白原眼眸微闪,眉宇间的凛冽之色缓了缓,忽然扬眉道:“听闻你如今是魔门护法?”
此话一出又惊得众人一跳,大当家与蝎子虎头看他的目光又变了变。在三域内,魔门的名声可比大雪山可怕多了。他们在三域横行时,也决计不敢招惹魔门中人,便是玄宗那样的庞然大物,其门下弟子也被蛮匪劫杀过,玄宗派人绞杀过他们,但只要跑得够快,他们便拿他们没有办法。
魔门却不同,他们比蛮匪还要神出鬼没,还要心狠手辣,曾经有一支蛮匪招惹啦魔门,不声不息的便被灭了全族,竟让人防不慎防。若要招惹魔门,定要将人全杀光,不露一丝痕迹方可,若被发现,便是灭顶之灾
并不在意众人的眼神,南寻殷笑着点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