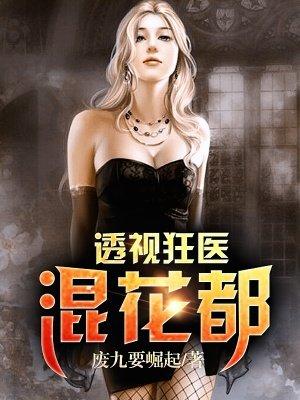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悍妃惊华全文免费阅读 > 第三十二章 前路珍重(第1页)
第三十二章 前路珍重(第1页)
第三十二章:前路珍重
苏长宁却罢罢手,止了莫闻人的话,“我一直以为面前只有死战到底这一条路可走,现在突然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条路可供选择,这是好事,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便是如此,所以大家放心吧,墨王应该不会杀我。”苏长宁平静的,又跟了句, “就这么办吧,”
看着如此情景,周策好像要赶走苏长宁的不是那位坐在龙椅上的至尊而是他这个巡查史,不然感叹道,“长宁,我们皆知你不是叛国之人,此去定当。。。。。。”
苏长宁闻言单膝跪地,笑了笑,故作轻松,“多谢两位大人心意,实在感谢之至,他日若还有机会重聚,定当设宴款待。”
周策的人情世故比许多人要阅历丰富,听闻苏长宁话语,品出其中味道,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叹道,“外患并不足惧,最怕就是内忧,所谓祸起萧墙,防不胜防。如今局势,国家存亡仅在呼吸之间,全国上下,理应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料不想。。。。。。哎。。。。。。”
苏长宁站起来,只觉有些感伤,茫茫太清,种种一切,都是一场似真还假的梦。十几年前, 是她的父亲将她送进尘世间最是硝烟弥漫残酷冰冷的所在,她从最初的战战兢兢闪闪躲躲,到后来的所向披靡覆雨翻云,她已经渐渐习惯渐渐认命。十几年来,正是这个地方,战火焦土的味道让她的性格一点点坚毅倔强,但身边之人一个个离去又将她的内心摧残的百孔千疮,也正是这个地方,给了她希望也给了她绝望,给了她可以骄傲抬头的资格,却也给了她向这个粗砺人世妥协的命运,可是,当她有时间这么安静的坐着审视自己的时候,却发现,原来自己骨子里还是那么耐不住寂寞,不然,为何会如此投入?正因为投入,所以在失去的时候才觉得心里那般的疼。苏家戍守了百年的北境疆土,自己戍守了十几年的信念,却是如此这般随着轻飘飘的话句说没有就没有了。
莫闻人也不再言语,前几次攻城,皆因苏长宁屡屡料敌机先,致令他们功亏一篑,而今,没有苏长宁的澜沧,看上去是如此地不堪一击。可笑的是,像苏长宁这样能战能守的忠勇之士,竟也是说罢官就罢官,说叛国就叛国了。大概天意,也是要亡他南陵吧。
苏长宁在澜沧城的大街上漫无目的的走,不知怎么就到了吴娘的屋子里,她将自己隔离在那片小小的土屋里,白日里努力控制的情绪终于起了波澜,然而苏秦的话却每次恰到时候的出现,总是那么魔咒的,把她向着苏秦心目中理想女儿的方向拉过去。“哭哭哭,哭有何用?你这个懦夫,遇事逃避的都是懦夫!”苏秦跳着脚暴燥的声音,和他手中挥动的鞭子,如同一根无法拔除的刺,隔着阴阳两界茫茫延伸过来,刺在苏长宁的心口。
突然一阵异响,苏长宁忙寻了一块瓦片在手中掂了掂,打算向着那人影飞出去。人影近了近,苏长宁却收手了,“哑狼。”她叫了声。哑狼站在吴娘的房门外,借着月色,她看清哑狼手中握着一封信,还有一件闪着绿色荧光的东西,她打开信,却只有一个字,一个硕大的“梅”字,写得气势恢迭,开合之间,杀伐隐现,但不嚣狂,反而有一种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气质,只有那个人才有这样的气质。
长宁接过那件闪着绿色荧光的东西,迎着月色一瞧,忽地脸色变了变,好像手里的东西千斤重,以致于让长宁都踉跄了一下,长宁看了看哑狼,道,“这些东西哪来的?”
哑狼连忙跪下,打着手势,显得有些慌乱,“我进来时看到地上有,所以就捡起来了……”
苏长宁背月而站,叹了口气,“雪公子。。。。。。”
其实长宁知道,很多东西在经意与不经意间错过,是再也找不回来,往日种种,似水无痕,冥冥之中,一切仿佛早已注定,求而不得。只是,长宁又看了看手中的东西,将它塞到袖中,那分明就是一柄锋利的刀子,她不知道这刀子对准的是谁的胸口,但她知道,如果一个不小心,这刀子第一击就会戳进自己心窝子。
商谊与雷神完全是明火执仗地在准备撤退,城内灯火通明,城上人影幢幢,成鹤已率领一部精锐已提前出城,第二批集中了大量的伤员则由商谊引命正做着出城准备,莫闻人则和雷点率另一部精锐断后。
点点星火在残破的城头之上飘飘荡荡,映着城头上下斑斑的血迹,都在忙着撤军,城墙上已无人看守了,长宁独自一人站在城墙上遥望着远处的北燕军营,那军营里灯火弯弯曲曲绵延了几里,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长宁低下头,这时束住一头秀发的簪子不知怎么就掉落下来,被风一吹一绺乌发垂下吹得微乱,她在地上找了半天然后站起来正欲将发往后拢,重新挽住的时候,抬眼间就发现城墙下有一匹雪白的马,雪白的马上坐着一个一身雪白衣裳的人,他的神情看不真切,但还是一如既往地潇洒傲岸、洒脱利落。
长宁手中的簪子不知怎么又不听使唤掉落在地,那头发胡乱的扑打在她的脸上。
宁越看着她将自己的头发想往后拢,可奈何风大硬是将她的头发往前吹,她正站在一盏灯笼火下,脸上略微带了一点恼意,与那风那头秀发较真的恼意。不一会长宁倒也不与那头发拼命了,就由着它散开随风舞动着,看了宁越一眼想理又不想理的转身欲走。
“苏长宁,你打算就这样走了?” 宁越气态从容语有笑意。
长宁转过身来,道:“你想留我做客不成?”
“我的确是来留你做客的,带你离开此地以免牢狱之灾。”
长宁笑了:“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的?”顿了顿,长宁又道,“你还真是心狠,想逼我坐实我的罪名么?”
“你是一名难得的好将。在南陵只会被埋没。”宁越道。
“可我毕竟是南陵的人。”
“我记得你说过,只要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并不在乎是否他国统治。此次北燕沿路南下,可有过扰民之举?”。
“没有。”
“可有在攻下州城后纵兵烧杀抢掠?”
长宁摇了摇头,“但这又不能当作是我判国的理由。”
宁越衣鬂微乱,但神色自若,脸上仍带微笑,他知道,有些事是必须交与时间的,唯有在时间中才会出现峰回路转的那一刻吧。一时宁越坐于马上,衣衫在风中飘荡。地上的霜已积聚了一些,厚厚的一层覆在枯草上。
彼此就这样望着,也未曾再去说些什么,四周只有一缕惨淡的月光投落在霜地上,却教白霜看起来更具了几分寒意,一时竟分不清是霜色还是月色了。
“长宁,此去前路珍重……”马蹄声声中,这句话隐隐约约的,被风卷起来又落下去,卷起来又落下去。
澜沧城军营里灯火通明,周策宣读完圣旨,商谊和着几位得力干将齐刷刷跪下,激动地说。“周大人,这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都尉一心为朝庭办事,并未做什么叛国之事,万不能凭着敌方几句话就先乱了分寸,现在兵临城下,这样做只会有失军心啊。”
周策将圣旨给苏长宁,这圣旨是早在他起程前墨王就秘密给他了,内中意思一旦苏长宁有叛国的苗头,立即命翼龙卫押解回都。主帐外围着一排翼龙卫,还有一排苏家军,翼龙卫统领修炎押缚着被捆成粽子的苏长宁走出来,又见更多的苏家军向这边聚集,跪倒在周策的面前,齐声道:“周大人明鉴,都尉忠心体国,绝对不会私通北燕,还望大人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