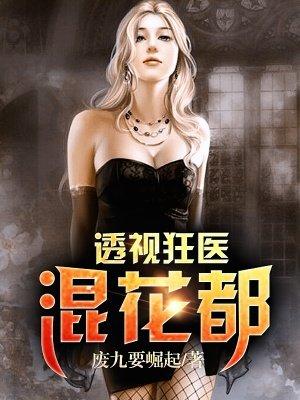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弗朗西斯在线 > 第84页(第1页)
第84页(第1页)
“满、满意。”记者不再追问,乔小洋虽然看着是个柔和软糯的人,但内里却比普通人要来得刚硬,吃过一次瘪后谁也不想再碰这种硬茬儿。临结束发言前,乔小洋望着朗闻昔说:“谢谢您,收藏我的作品。”一个‘您’字疏远又陌生。朗闻昔直到自己上台介绍自己的作品前都处于一个浑浑噩噩的状态,而且被成寒念叨了好几回,付斯礼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的牵起了朗闻昔的手,踹进了自己口袋里。上台前他捏了捏他的手指尖,说:“该你了,我的大画家。”朗闻昔走上台时,灯光打在了他的身上,打着绷带的手臂让他看起来带着一种脆弱的破碎感,刚哭过的眼睛又带着一种莫名的明艳感,这种反差的视觉效果,让台下的人都忍住想要多看他两眼,这大概就是艺术家的本身也成了一种艺术品。拍卖会的主持人按照流程开始cue朗闻昔回各种问题,从他这段时间的经历再到他的作品,朗闻昔的回答都非常的简单,可以看出来他很不在状态。一直到主持人问道今后打算在国内发展还回西班牙发展时,朗闻昔的眼睛才亮了亮说:“在国内。”“为什么?”“因为,我想有个家。”朗闻昔说着,看向了一楼的付斯礼。在听到这个答案和接收到朗闻昔的目光时,付斯礼的呼吸一滞,心脏也跟着一阵收紧,他紧握的手掌开始出汗。糟糕!朗闻昔这也太犯规了吧!付斯礼想立刻冲到台上把人抱下来,扛回家。“闻昔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幅拍品?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给创作带来了灵感呢?”主持人问道。“我的回答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并没有。只是为了画而画,这些都是我开工作室后的作品,对我而言更像是商品,有些经历和思考都停留在了学生时代。当步入社会后,我的驱动力好像都源于能够更好的生活。我不是一个有才情的人,我活的比较铜臭,我第一张卖出的画叫《空沙发》,在十年它卖了2000块,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是笔巨款。”朗闻昔说着,眼神暗了暗。如果当时没有卖掉那幅画,也许没有今天的自己,但他和付斯礼也不会错过那么多年。“自那以后我就知道这只是一门手艺,但我的老师安德烈先生说过,艺术最大的价值就是让创作者能感受到其给予创作者本身的获利,或金钱或情绪宣泄或自我满足的同等价值回报。所以,每当我创作完一幅作品,我能满足于自身的任一一种需求就好,就像我今天站在了这里。”朗闻昔说完看向了付斯礼,他看到了付斯礼眼中的惊讶,他看到付斯礼和成寒在说话,也大致猜到了他们在说什么。付斯礼问成寒:“朗闻昔说的安德烈是安德烈·曼德?”“你怎么知道?他好像没有公开说过全名!”成寒也只听朗闻昔提过一次。因为这是他母亲的情人——安德烈·曼德,母亲回来不久之后,他们就分手了。他也并不知道这位母亲的情人是做什么的,他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母亲回来的当天,一次是他们送她回国的时候,那天发生的一切都让付斯礼印象深刻。——朗闻昔也是那天离开的。有些事情似乎在慢慢的串联起来,付斯礼突然觉得眼前的朗闻昔藏了许多的秘密。“我们家的大画家还是那么会说,嘿嘿,这措词绝对会让楼下的那波人买账,毕竟有些情怀比不上艺术家的个性。”成寒边说边晃着香槟酒杯。朗闻昔的三幅作品一共拍出了220万,一晚上进账175万,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这是一年不开锅,开锅吃三年。”成寒笑嘻嘻地看着自家的摇钱树走过来,卸去了艺术家的伪装,朗闻昔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走到了付斯礼的面前。“还好嘛?”付斯礼抚上了朗闻昔的肩。朗闻昔没精打采地嗯了一声。“我约到了乔小洋,我觉得你们可以谈谈。”说完,付斯礼又在朗闻昔的耳边低语了一句:“我陪着你。”十分钟前,付斯礼在洗手间里遇见了乔小洋,一旁的私人护工正将助行器递给他,他冷着脸瞥了一眼对方说道:“说了多少遍,我可以!出去!”说完,乔小洋费力地用单腿支持起了身体,手扶着栏杆进了隔间。乔小洋出来的时候看到付斯礼的站在洗手台前正等着自己,他有些局促地收回了自己眼神,紧扒着栏杆想要挪回轮椅上。可是没想到自己的私人护工却忘了将轮椅固定住,他正要坐上去的时候轮椅直接向后滑开,好在付斯礼眼疾手快一只手撑住了轮椅,另一只手托住了他的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