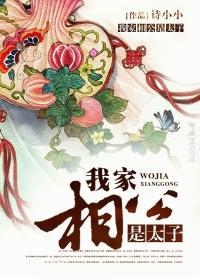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春日降至 > 第154章(第1页)
第154章(第1页)
撑开的扇子似的,偶尔扑簌两下。投落阴影,也衬得眼里的亮光璀璨。
贺知宴盯着她,喉结微动。
原莺捕捉到,不满:“你又在想什么呢?网上专家说,要节制,不然伤身——”
他说:“你在发光。”
“……”原莺关掉手磨:“……啊?”
贺知宴的手指抵在太阳穴上,目光认真地掠过她身上每一寸。
“你好像比别人都亮一点,”他思索着:“从小时候就是。”
原莺自得:“我皮肤白嘛!”
贺知宴:“不是这个意思。”
原莺疑惑地歪头。
“算了,”他一时也解释不来:“你继续。”
“……哦。”
原莺换了一把小型刻刀。
在工具嗡嗡的声音里,浮灰溅起又沉下。
屋里的光线西落,贺知宴没有去开灯,他刀削斧凿的面孔,逐渐被暖灰色的天光笼罩,沉默得像一座石膏雕塑。
原莺终于关掉刻刀,吹了吹木屑。
“我好了!”她兴高采烈地展示:“你看,是不是很可爱?”
她讲出“可爱”这两个字,就注定这个木雕不会合贺知宴的心意。
贺知宴抬头看去。
大头小身。
尤其卡通的形象,配上她刻的歪歪扭扭的五官。
贺知宴看得眼皮一跳。
“这和我哪里像了?”
“不要强求嘛,”她坐到贺知宴身边,把木雕塞到他的眼前:“你以前刻的铅笔都看不出五官呢,我还有细节。你看!”
她指着圆形的手中间一个坑:“喏,你手上的痣。”
贺知宴:“是你刻坏了吧。”
原莺:“不要揭穿我嘛。”
贺知宴接过她手里的小人,收进怀里。
原莺:“你不是不喜欢吗?”
贺知宴:“我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