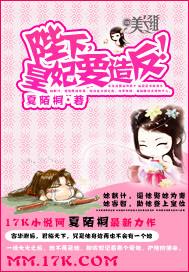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的的结局 > 第166章(第1页)
第166章(第1页)
&ldo;遗憾的是党没有看到它的捍卫者休息的重要性。疲倦的人是要出错的,谢尔差&iddot;尼古拉也维奇。&rdo;
葛洛甫科凝视着盘中的鸡蛋好长一阵,然后把他的嗓音压得更低,&ldo;克列门蒂……让我们暂时假设我知道一个高级克格勃军官在会见一个高级中央情报局军官。&rdo;
&ldo;有多高级?&rdo;
&ldo;比局长还高。&rdo;葛洛甫科答复道,告诉了瓦吐丁究竟是谁而没用一个名字或职称,&ldo;让我们假设我安排了这些会见,并且他告诉我说我不需要知道会见的内容是什么。最后,让我们假设这个高级军官行动……反常。我应该怎么办?&rdo;他问道,被告以一个直接从本本上找来的答案:
&ldo;当然,你应该为第二局拟定一份报告。&rdo;
葛洛甫科差点让他的早饭呛着,&ldo;一个好主意。紧接着我可以用一块刀片割穿我的喉咙,省却人人来审讯我的时间和麻烦。有些人是不可怀疑的‐‐或者有足够大的权力,没有人敢怀疑他们。&rdo;
&ldo;谢尔盖,如果在过去几星期里我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没有&lso;不可怀疑&rso;这样的事情。我们一直在搞一个案子,在国防部所涉及之高……你将难以相信。我简直不相信。&rdo;瓦吐丁向一个服务员招招手,让他带一壶新茶来。这一停顿给了另外一人一个思考的机会。葛洛甫科因为他在战略武器上的工作,对那个部有深刻的了解。那会是谁?没有很多人克格勃不能怀疑‐‐那不是这机构想要促成的状态‐‐在国防部高处的人就更少了,既然这个部克格勃应当以最强的怀疑态度来对待。但是……
&ldo;费利托夫?&rdo;
瓦吐丁脸变得苍白,接着出了一个错:&ldo;谁告诉你的?&rdo;
&ldo;我的上帝,去年他给我通报了中程武器的问题。我听说他病了。你不是开玩笑,是吗?&rdo;
&ldo;这事可一点儿逗乐的东西都没有。我不能说多少,而且这事不能离开这张桌子,但是‐‐是的,费利托夫在为……在为我们国境外的人工作。他自白了,并且审讯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rdo;
&ldo;但他一切都知道?武器谈判小组应该知道这事。这改变了整个谈判的根据。&rdo;葛洛甫科说道。
瓦吐丁没有考虑到那点,但他没有权力作决策。他毕竟只是一个有专项特长的警察。葛洛甫科作的这个评价也许是对的,但规则就是规则。
&ldo;这条消息目前保密很紧,谢尔盖&iddot;尼古拉也维奇。记住这点。&rdo;
&ldo;情报的独立分块能助我也能逆我,克列门蒂,&rdo;葛洛甫科警告道,不知道他是否应该警告谈判者。
&ldo;这很正确,&rdo;瓦吐丁表示同意。
&ldo;你们是什么时候逮捕犯人的?&rdo;葛洛甫科问道,并得到了他的答复。这个时机……他呼了一口气,把谈判忘到一边了,&ldo;主席至少两次会见了一个高级中央情报局军官……&rdo;
&ldo;谁,什么时候?&rdo;
&ldo;星期日晚上和昨天早晨。他的名字是瑞安。他在美国小组中是我的对手,但他是个搞情报的,不跟我一样曾是外勤人员。对这点你怎么看?&rdo;
&ldo;你肯定他不是一个搞行动的?&rdo;
&ldo;肯定。我甚至能告诉你他工作用的房间。这不是一件不确定的事。他是一个分析专家,一个高级分析家,但只是办公桌前的人。他们的分管情报的副局长的特别助理,在那之前,他是驻伦敦的高级联络小组的一员。他从没有出过野外。&rdo;
瓦吐丁喝完他的茶,又倒了一杯。接着他用黄油抹了一片面包。他不慌不忙思考着这事。有足够的机会来推延答复,但是‐‐
&ldo;我们所有的只是不寻常的活动。也许主席在进行什么事情,而此事是如此机密……&rdo;
&ldo;是的‐‐或者说这事表面上看起来应该是这样。&rdo;葛洛甫科评论道。
&ldo;作为一个&lso;一&rso;字号的人,你似乎有我们的思维方法,谢尔盖。很好。我们通常要做的‐‐倒不是象这样的案子,很通常,不过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汇集情报,并且把它上报给第二管理局局长。主席有警卫员,他们将被带走审问。但这样的事情必须很谨慎、很谨慎地处理。我的首长必须去见‐‐谁?&rdo;瓦吐丁修辞性地问道:&ldo;一个政治局成员,我想,也许中央委员会书记,但是……费利托夫事件是在很隐密地处理着。我相信主席可能希望用它作为政治筹码来对付国防部长和瓦涅也夫……&rdo;
&ldo;什么?&rdo;
&ldo;瓦涅也夫的女儿在给西方当间谍‐‐噢,准确地说是一个跑差。我们制服了她,并且……&rdo;
&ldo;为什么这没有公诸于众?&rdo;
&ldo;奉主席之令这女人又重返她的工作。&rdo;瓦吐丁答复道。
&ldo;克列门蒂,你知道这究竟是他妈怎么回事?&rdo;
&ldo;不,现在不知道。我假定主席想方设法地加强他的政治地位,但是会见一个中央情报局的人……你肯定这事?&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