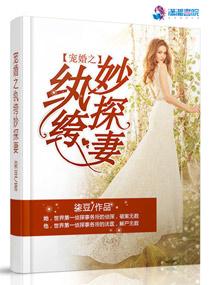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穿越到安史之乱当医生的电视剧 > 分卷阅读61(第1页)
分卷阅读61(第1页)
如今局势动荡,事端异生,听朗之说陈留有身份不明的胡人出没,我不得不挂心啊。”
说完,他将手指轻轻扣在案面上,目光在灯影中明晦不定。
王焘缓缓收回手,明白了对方夜请自己的目的。
“老夫已经致仕,朝堂上的事恐怕不能为郭公与伯瞻分忧。”
他伸出手,旁边的年轻人便立即递上纸笔。王焘一边伏案写方,一边平心静气地道:“至于那突厥少年,于老夫而言只是病人。而老夫如今也不过是个医者。”
他将写好的药方折了两折,交给谢照。
“王公误会晚辈之意了。”谢敬泽叹道,“您是医者仁心,自然对所有病患一视同仁。而我等为官宦,为了百姓则不得不有取舍。不瞒您说,近来晚辈这里也吹来些边地的风声,所以心绪难安,辗转难眠,才特特请了前辈来。”
这话说得恳切。
于公,王焘是六朝元老,见惯了风云变幻。于私,他亦是谢望的恩师,更是谢敬泽一直仰赖的前辈。所以他今夜请王焘来,并不为指摘官医署里的事情,而是希望对方能指点迷津。
王焘注视着他紧绷的面容,唇角含了淡而深远的笑意:“伯瞻可曾听说过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韩非子的文章谢敬泽自然是读过的,他点点头:“扁鹊数见蔡桓公,告知其病情,而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而死。”
话到这里,他似乎有所领悟:“您老的意思是……”
“人之有疾,不应惧怕医治,有时甚至需要用刀割去病灶。虽难免疼痛,但正所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王焘的目光,不因年迈而显得迟钝,雪亮地看向对方,“医者治人,相者治国,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谢敬泽神情微微震动,起身恭肃地行了一揖:“晚生受教了。”
王焘笑着摆摆手:“老夫不过是和你说些行医所感罢了。”
见天色已晚,谢敬泽便也不再留他,令谢照亲自送这位老前辈回府。直到走出谢府,王焘才似承受不住地咳嗽两声,脸上露出隐忍之色。
谢照担忧地搀扶着他:“王公,您……”
“不妨事。”缓过一阵,王焘才松了眉头,“老夫已老,很多事情也无能为力,你父兄都是重责重任之人,还需你多行开解才是。否则忧思过重,难免伤身。”
谢照便不再多言,颔首道:“晚辈明白了。”
几个时辰后。
天空白了一线,初升的日光穿破云层,由远及近,逐渐将整个陈留城照亮。仵作房的小院中,三双熬得通红的眼睛齐齐盯着慢慢退去火红的陶器,看着李明夷伸手将盖子揭开。
“这就是甜油?”
被李明夷期盼已久的新物质,正似油一般浮在水面的上层,看上去透明清澈,闻着却是刺激扑鼻,带着一种古怪的甜味。
经历了一整夜的失败,不断调整火候,比例,报废了无数个陶锅,还险些把院子都点着了,拢共才熬出这么小半碗甜油。
马和实在想象不到,这种油有什么特别之处。
张敛亦费解:“它可以将人麻醉?”
李明夷小心翼翼地将得来不易的甜油慢慢倒入一个碗中,用手扇动气味,轻轻嗅了一下,确定地点点头。
不过第一次制备出来,要检验其功效,肯定不能用在人身上。
他目光四处转了转,忽然落在门口那头恹恹闭着眼睛的毛驴身上。
尚在梦乡中的毛驴,仿佛感受到注视的视线般,猛然惊恐地睁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