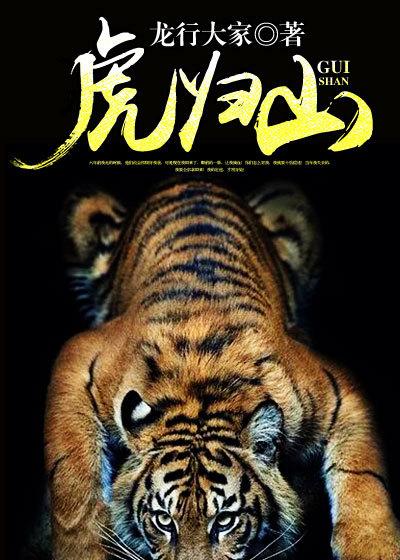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锦水东北流 > 第三百一十一章 打情(第1页)
第三百一十一章 打情(第1页)
分析的这样头头是道,当真以为替他好姐姐打算?
啊呸,可千万别信他嘴上那套,实则,他一点儿也不着急,更莫论替他好姐姐打算。
夫人?填房继室?做梦呢吧。都是他那不省事的娘日夜拱火烧的,他那娘就是个做梦想屁吃的疯癫货!
提起这事儿就想骂那疯婆子。
合着现在待遇也不差,老实做个能捞会赚的姨娘不好吗?非撺掇她往不相干的上头想。
夫人夫人,蠢妇们成日里算计名分。有了馒头想肉,有了梯子想上天。还想妃子娘娘呢,还想皇后呢。
还扶正,她高盼儿指着脸扶正呢。吃灯草灰,放轻巧屁,这事绝不是这些娘们想的那样简单。
那姓周的都定下了,这姐姐还蒙在鼓里做夫人梦呢。
所以他什么都知道,却嘴严的撬不开。姐姐长姐姐短,只是不吐口。
他偏不直接道明,他晓得高盼儿满眼、满心、满脑、满腹、乃至整个人生充斥着夫人梦。
忽喇喇的告诉她做不成,犹如拿刀开她天灵盖。戳破这夫人梦,她会疯会死,这坏人他不做,这实话他不说,他只是在试探。
果然,这妇人离疯魔也不远了,那就更不能说了,有梦且做着吧。
摇着扇子,咕噜噜在真儿身上转着眼珠子。
那真儿也不畏,低眉颔首,一双玉手把个帕子来来回回的绞,还不忘拿眼横他。
哎呀,这冤家!正好撞在他玩味十足的眼神中,登时小鹿乱撞,红霞满面。
他横她,她剜他。
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目光痴缠。情欲在压抑中膨胀,好一个郎情妾意。
沉浸在悲伤中啜泣的妇人浑然透明,看不到,听不见,这场面好不滑稽。
只见那高鹏举端着盏,目光越过他哭泣的姐姐,只顾拿眼调情。
“哗”一个没注意,茶泼了,盏落了,衣潮了……
“噗”真儿忙咬唇憋笑,高盼儿回神,盯着他看,这一幕拨雨撩云方止歇。
他也笑,猥琐油腻。“呼啦”收了扇子,给高盼儿递过帕子。
“可听说南迁的事?外头疯传,天家要南迁,姐夫这儿可也听到些言语?”
“南迁?为什么要南迁,往哪迁?我不走,这偌大的房宅田土,说丢就都丢了?天家想一出子是一出子呢。甚南迁,我没听过。”
定定赌气又说:“我不管,管他南迁北跑,我只要坐稳我的夫人。”
“少扯没用的,快些张罗扶正的事才是要紧,要紧。”
“榆木脑袋死没用的愚妇!”
高鹏举竟指着鼻子骂了起来,胆儿肥了呀。
“打仗,知道什么是打仗吗?还惦记你那一亩三分地,甚夫人、宅院、细软、头面,打起仗来都是一堆灰。狗屁的南迁,就是逃跑、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