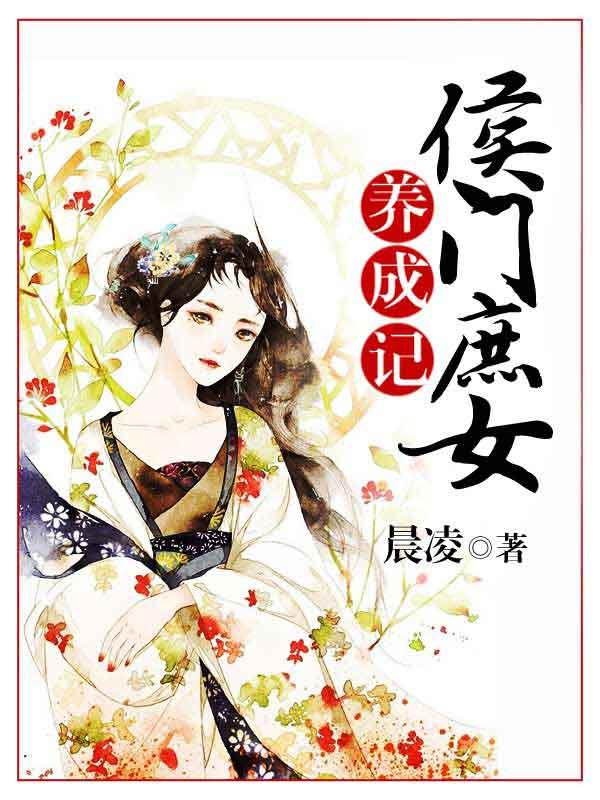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情人关系一旦超过六年 > 第37章(第2页)
第37章(第2页)
他对着林烝倒是一点头:“林总,桑总,我这就走了,一会儿晚了怕没回市里的车。”
桑野抽着烟没理他,林烝也就淡淡一点头,许卿嘱咐他:“路上注意安全,到了微信上和我说一声。”
辛期在许辅导员面前笑起来十分阳光,点头说好,藏了甜头的喜悦年轻人藏不住,桑野别开眼去偷笑他,没人拆穿这种朝气,因为那是鲜活的、不谙世事的、无忧无虑的甜蜜。
辛期遥遥地和他们挥手,去往垂钓台下边的车队等车。
桑野远远看着他的背影,又叹了一句:“年轻真好。”
许卿脸上的笑意稍淡:“桑总这话说得好像没有年轻过一样。”
桑野抽了口烟,望向大学生背着背包离开的方向,淡淡说:“的确没有。我没有像他那样年轻过。”
林烝淡淡地看着他。
桑野也是鲜活的,看起来不谙世事的,看起来无忧无虑的。
也只是看起来。
成年人有诸多烦恼,可他少年时也没什么可以称之为幸福的乐趣。
“我没有像他那样年轻过”,这句话背后有些心酸和委屈,他的确没有在少年时候真正快乐过,成年之后有了不错的经济能力,张扬放肆的那几年里,也的确没有长长久久地爱过一个人。
爱情于他是恐惧,是深渊,是毒药,是蒙彼利埃墓地里一方小小的远眺东方的坟墓。
他渴望爱情,又排斥爱情,于是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换了一个又一个的情人。
他和他爱过的那些人都是一往无前的直线,只相交于生命中短暂的一个点。
桑野说的时候像是在开完笑一样轻声无情,寡淡。
许卿拍拍桑野的肩,转开话题说:“闹人的小孩儿也送走了,我们往河上游个船再下山,差不多又该吃饭了。”
“吃饭吃饭,”桑野跟在许卿身后孩子气地抱怨两句说,“什么时候能一事休万事休,休了要吃饭的五脏庙啊?”
许卿笑他小孩儿脾气:“修仙啊你?”
桑野啧啧嘴。
从垂钓台往下走,右手边通往车队,左手边近水,有一个不大点儿的码头,旁边停了一溜的渔船,只有两艘稍微大一些,涂着红漆花带,花的样式有些老土,但还算不错。
更惹人眼睛的是那一溜的渔船,上边的大大小小停了一群的鸟儿,通体漆黑,只有面颊上留一道月牙白。
“这是什么?”桑野有些好奇。
“鸬鹚,鱼鹰,”许卿说,“当地人叫它水鸦,用来抓鱼的。”
桑野大概听说过,不过那都是很小的时候,还未出国的时候在课本上读到过的课文,他有些记不太清了:“是不是那个被人拴住脖子,抓了鱼不让吞的那种鸟。”
许卿听他这种介绍微微皱了眉头:“对,就是那种鸟。这里的人大多是从外边回来的渔民,听见这边可能会拆,改造成旅游度假区,好些人被召回来组织水上的捕鱼表演项目,可古庄还有泉镇目前根本养不起这么多张嗷嗷待哺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