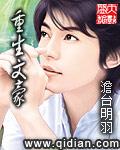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隐公元年注疏 > 第9章(第1页)
第9章(第1页)
退一步论,即便能够确认《春秋》确实是孔子所作,但王说还只能算是入情入理而已,铁证依然渺茫。
毕竟,对答案的评判不能只看它是否合理,因为合理的答案未必就是正确的答案。在若干个合理答案之中,“更合理”或者“最合理”的那个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不是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只按照理性行事,也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所有记载更不会毫无遗漏地告诉我们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环节。于是,事件常常是需要拼凑的,“合理”常常是存在缺环的,不合理的答案未必是不正确的。
7.效法天数:最“不合理”的答案也许才是正解
一个“不合理”的答案带着证据出现了。曾被王充狠狠批驳过的“《春秋》十二公为效法天数”之说在两千年后又以崭新面目伴随着崭新证据而重现,这证据是两件青铜器:秦公钟和秦公簋。
张政烺从这两件青铜器铭文入手,阐述着“十二”这个数字在古人的眼里如何意味深长。张文题为《“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60大意是说:
秦公钟和秦公簋的铭文都有“十又二公”字样,看来这是指秦国国君世系上的十二位先君,但这“十二公”到底是怎么回事,历来让人费尽猜疑。秦国的十二公和本文并无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是:“十二”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张文引述了《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的一句话:“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周朝称王天下,制订礼制,其中规定了上等物品的数目不超过十二。)这话的背景是鲁哀公和吴国人的一次外交活动,当时吴国人提出的送礼数额是牛、羊、猪各一百头,子服景伯认为凡事都该按规矩(礼)来,送礼送多少,周礼都有详细规定,而周礼对上等物品数量的最高定额就是十二,因为这个数字是“天之大数”。
《左传》杜注是:“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大意是说:天有“十二次,所以制礼的时候对此予以效法。”张说:“‘十二次’是天文学家的术语……古人认为岁星(即木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所在的位置叫作一次,故周天有十二次。但是,十二年绕天一周这个周期太长,一般人不会留心每年岁星怎样移动,十二次在非天文专业人员的头脑里不会形成一个概念,因此也就不大可能把它当作天之大数。古人最早知道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是天之大数首先是从十二月来的。”
古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十二”这个“天之大数”的效法并不罕见,就连作衣服也要体现这个数字:“《礼记·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从天子祭天之服,贵族闲居之服,到庶人的礼服,都要在十二这个数目字上做文章,这便是法天之数。”
还有一个重要线索出现在《史记》当中:过去的学者大多认为《史记》的十二本纪在体例上是仿效《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可见司马迁是预先定下十二纪之数,然后再填充内容。《史记》十二本纪很难说是个合情合理的编排,比如,刘知几就曾认为《秦本纪》(自伯翳至于庄襄王)、《项羽本纪》应该归在世家,称本纪是自乱其例。对这种“自乱其例”,司马迁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大原则是“十二”这个数字是不能动的,本纪的十二个座位必须被填满才行,可历史人物很难与人为规定的数字完美对应,司马迁不得已之下这才“自乱其例”。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有学有识,为什么把《史记》全书的纲领搞得这么糟?这是受家学的影响——司马氏世为天官,星历是他家门的本行,世代薰染不易摆脱,本纪要有十二篇才足以显出神圣庄严,否则便不成个体统,法天之数是学者的职责,相反则成为街谈巷议的小说了。……十二是成数不能变动,内容不足则杂凑,如果多呢?则采取压抑的办法,以多报少。《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白说“谱十二诸侯”,而内容是十三国……”
回到《春秋》的问题,张政烺匡正王充之说:“王充的精神是科学的,其所驳斥皆流俗经师之言,破除迷信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应当完全肯定。但是,要了解古代的历史却未必能见真相,因为古人(从孔子到何休)都是在迷信的圈子里长大的,怎么能使他毫不沾染呢?所以我们的看法恰和王充相反,‘春秋十二公’本来是法象天之大数……”
确实,《史记》列五体,篇目数字各有涵义,使全书构成了一个“人工创作的系统工程”。61若不明白汉人的迷信观念,便很容易认为司马迁的编写次第毫无意义。62同样,虽然在现在来看,“《春秋》十二公”效法“天之大数”显然过于形式主义,很不合理,但这种思想在孔子当时的社会上却是再平常不过的道理。
那么,如果是为了凑数的话,孔子作《春秋》的难度应该比司马迁作《史记》要低一些,因为司马迁要在一个通史的框架里捏合“十二”之数,而孔子只要从自己所生活的鲁哀公时代往前推出鲁国的十二位国君即可——推到第十二的时候,正好就是鲁隐公。
这的确是个“不合理”的答案,但是,对数字的附会,古往今来比比皆是,尤其汉代,“汉朝人对于数字的神秘性是如此的入迷,他们甚至可以牺牲观察的精确来迁就迎合一些神秘的数字”。63其后,再如话本中的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数字即取自于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之和。如果继续追问三十六和七十二的来历,大约还能追溯到五行理论上去。64《周礼》描述官制,按天地和一年四季分为六大系统: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65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通篇都在讲官制和数字的关系,这正是汉家“天人合一”之一例。其中说到朝廷以十二臣为一个单位,效法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66——杨希牧曾经给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以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定性:“董氏可以说是中国甚或全世界学术史上最早从事宗教符号学研究,并最先使用现代所谓‘符号’一词的一位符号学家。……该书(即《春秋繁露》)未尝不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符号学的论著。”67如此看来,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以符号学家的姿态在作着破解《春秋》密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