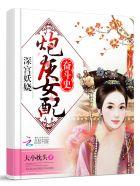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隐公元年注疏 > 第93章(第1页)
第93章(第1页)
杨在这里还特意强调了《春秋》对时间记载的所谓义例:当初鲁国史官记录国家大事,肯定都有一定之规,时间上日、月相承,可现在我们看到的《春秋》却有时候有月有日,有时候有月无日,孔子作《春秋》不可能体例如此混乱,所以这些细微差异一定是暗示着他的思想精义,读者需要认真体会才行。833
钟文烝尤申此义,说《春秋》体例谨严,就算有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但还要按规矩记录一下日期,更何况是这等重要的国际会议?所以说,《春秋》取材于鲁国历代的国史,在这段话里本来一定是记载了具体日期的,只是圣人在后来编纂的时候因为看到后文有背盟之事,这才为了表示褒贬而把日期抹掉。——钟由此而把《春秋》推上了一个高度:《春秋》的行文风格是“前后相顾,彼此互明”,这是圣人的宏伟构思,如果我们仅以史笔衡量之,那就太小看圣人了。834
钟在这里清晰道出了经学主旋律:经学是经学,史学是史学;经学是至高的政治哲学,是圣人的经天纬地之术、万世常青之法,其地位远非史学所能及。835而在经学的光环之下,史学也难免受着“春秋大义”的引导,褒贬的意图总在汗青之中刻意凸显。伟大如司马迁,既是孔子的崇拜者,又在董仲舒门下接受过公羊学的专业训练,《史记》便多有效法《春秋》笔法之处。
话说回来,虽有了“善恶两举”的说法,但我们还是不能明白:这次会盟看来是鲁隐公主动发起的,后来在鲁隐公七年鲁国攻打邾国应该也是鲁国率先发难,到底该表扬谁,又该责备谁背信弃义呢?歧说如云,越深入越容易迷惑,以下便要求助于《左传》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了。
(八)《左传》经解: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1.名、字之辨
《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译文】
鲁隐公元年三月,鲁隐公和邾仪父在蔑地会盟。邾仪父就是邾国国君,名克。之所以《春秋》没有按爵位来称呼他,是因为邾国还没有得到周天子的封爵册命。称“仪父”,是抬举他。鲁隐公刚刚摄政,想和邾国交好,所以发起了这次蔑地之盟。
《左传》首先就和《公羊传》、《榖梁传》出现了一个史实上的分歧:怎么变成鲁隐公主动向邾国交好了呢?这个矛盾恐怕很难解释了。
再看称谓问题,《左传》的风格比较朴素,相比其他两传而言,多是就事论事,《左传》之所以说邾仪父就是邾子克,据学者们推测是因为《春秋·庄公十六年》提到过“邾子克卒”,虽然这很难说是什么过硬的证据(比如前文提到过的方苞的怀疑),但历来都是这么讲的。《春秋》一经三传,人物称谓之混乱,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阅读障碍,经常要前后检索、多方联系。
邾仪父的称字,在《左传》里同样是个问题。杜预解释说:附庸小国的国君并没有受到周天子的封爵,照例应当称名,但鉴于邾仪父能与大国(即鲁国)交好,所以称字来表扬他。836
杜预这里谈到了一个“照例”,又是说到《春秋》的编写体例,圣人多少的微言大义即蕴涵在种种或显或隐的体例当中。但孔子已经没机会站出来说话了,也不知道杜预的这番“发掘”是否准确。杨伯峻怀疑地说:通篇看看《春秋》的编写体例,发现凡是小国,或是文化落后的,或是地处边远的,所谓蛮、夷、戎、狄,其国君都称“子”。837
那么,到底是“例称名”还是“例称字”呢?如果是前者的话,本该称名而称字,是为褒;如果是后者的话,本该称子而称字,这是不是贬呢?——这真是一字之差,褒贬大异。
如果抛开字面的纠缠,思考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也许可以判定出邾仪父到底是该褒还是该贬。《左传》只说了“称“仪父”,是抬举他”,并没有具体交代为什么要抬举他。贾逵、服虔认为:邾仪父看鲁隐公是个贤君,是个孝顺的谦谦君子,所以愿意与他结好,而孔子为了表扬邾仪父,于是称字以示褒。——但贾、服这两位汉代经学大师似乎在这里犯了一个常识错误:传文里明明是说鲁隐公向邾仪父求好,而不是邾仪父向鲁隐公求好,所以,邾仪父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表扬的呢?
孔颖达就这样质疑贾逵、服虔的意见,进而举例说:《春秋经·桓公十七年》说“公及邾仪父盟于趡(cui)”,书法体例一如当前这句,这位鲁桓公并非贤君,但经文仍称“仪父”,这样看来,贾逵、服虔的解释就很难成立了。
但是,孔颖达这里恐怕有个小小的疏漏——《春秋经·桓公十七年》的这句经文是“公‘会’邾仪父盟于趡”,而不是“公‘及’邾仪父盟于趡”,这一字之差,若按前述《公》、《榖》两家的讲法,显然背后的意思大有不同。这也许是孔颖达的疏漏,也许是版本流传中没校出的错别字,因为孔就在前文还辨析过“会”与“及”的区别。但无论如何,经文确实是对邾仪父又称了一回字的。孔有破有立,继续解释说:附庸小国不能上通天子,也不参与会盟,如今邾仪父能与大国通好,孔子应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称字来表扬他的,而不是因为邾仪父仰慕鲁隐公是个贤君。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