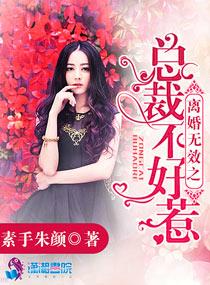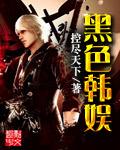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隐公元年注疏 > 第162章(第1页)
第162章(第1页)
当然,抛开政治因素不谈,胡安国的《春秋传》继承了北宋学人的苛评原则,浑身充满道学色彩,重义理而轻史实,仅以这几点而论,或许可以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高标独树,若要拿到清代汉学的阵营里,却绝对算不上什么佳作。
从克段一事上可以略窥胡安国的解经风格,他说:用兵是国之大事,需要君臣合作才行,所以用兵之事当称国命才对;讨伐叔段,公子吕作主帅,则当称将;派出了二百乘军队,则当称师。而《春秋》既不称国命,也不称将、不称师,只称“郑伯”,是认为罪过全在郑伯身上。单是这样还嫌批评的力度不够,所以又接着写“克段于鄢”——克,是表示以武力取胜;对叔段不称弟,是说郑庄公分明把叔段当作路人;于鄢,是说郑庄公对叔段迫之太甚。1466
胡安国虽然为《春秋》重新作传,却绝没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坐终始”,就在这一小段里,史料上得自于《左传》,义理辨析上得自于《公羊传》,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最后解释“于鄢”说“操之为已蹙矣”,这就是引自《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的文字,就连使用方法也是一样的,1467甚至在训诂上都是得自于何休的。
更要紧的是,胡安国的这个议论大异前人。以往一般都是说叔段坏、郑庄公更坏,而胡安国却说《春秋》之义完全是批评郑庄公的。胡安国也知道自己的意见比较特别,接下来便发出一个设问:所谓“君亲无将”,叔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犯的是必诛之罪,而郑庄公只是拗不过母亲而已,为什么说《春秋》放过了叔段而独独归罪于郑庄公?1468
“君亲无将”,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已见前述。那么,按照“君亲无将”的准则,叔段只要动了一点谋逆的念头就该被赶紧杀掉,既然如此,郑庄公就算这时候杀了叔段也是符合春秋大义的,被褒奖还来不及,怎么还会被批评?更何况叔段何止有一点点谋逆的念头,分明是荷枪实弹地把谋逆付诸实施了,《春秋》为什么放过叔段而独罪庄公?
胡安国的回答是:郑武公还在世的时候,姜氏就一心想立叔段为接班人,等到郑武公去世之后,姜氏以国君嫡母的身份主于内,叔段以国君宠弟的身份居于外,况且叔段多才好勇,很得国人的拥戴。郑庄公把这些看在眼里,恐怕叔段终将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故而费尽心机,纵容叔段走上邪路,然后再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到这时候,国人不敢不从,姜氏不敢掣肘,叔段自会被革除属籍,无法再居于父母之邦。这一切后果都源于郑庄公的心计。而王者之政是以德行教化民众,以自身的道德光辉感染民众,哪能用险恶心计对待天伦之亲再加之以刀兵?《春秋》探究事情的本质,首先要诛灭的就是人的不良动机(“《春秋》推见至隐,首诛其意”),以此来正人心,并昭示天下为公,不可因私乱公的道理。1469
胡安国在这里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春秋》学命题:“《春秋》推见至隐,首诛其意”,这就意味着,虽然叔段恃宠而骄,终于走向谋逆之途,但这主要是郑庄公刻意养成的,所以祸根还是得算在郑庄公的身上。
《春秋·桓公十一年》记有“郑伯寤生卒”,饱受后人争议的郑庄公就在这一年里辞别人世,而胡安国继续批评道:作为一国之君,所作所为一定要遵循天理,可不能让私欲压倒天理。郑庄公之事是我们永远的反面教材。1470
这里明显看得出二程的渊源,问题说到最后,终于归结为天理与人欲之辨,而重动机不重结果也是理学的一个主要观念。1471至于胡安国对用兵的意见,这里讲君臣合谋,后文则强调兵权不可假人,这确是尊王之道,对攘夷却难免掣肘。王夫之即对此深以为憾,说胡安国对秦桧以管仲、荀彧期之,而胡氏此论也深合秦桧之旨。1472尊王与攘夷,有时候并不那么统一。
6.真德秀
(1)淮南王刘长案例
真德秀《大学衍义》引述了胡安国对克段一事的议论,后面还有一句,说在郑庄公死后,嫡子出奔,庶子为君,诸公子互相争斗,乱相愈演愈烈,而祸乱之源,“起于一念之不善,有国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灭之也”。1473道德政治之说,天理人欲之辩,这是南宋理学家眼里的经学世界。后来愈演愈烈,理学家所恒言的,常是孔子所罕言的。1474
真德秀是南宋理学大宗,是朱熹的再传弟子,程朱之学被洗脱“伪学”罪名并被立为官学,真德秀居功至伟。儒学至南宋,风气由外王转入内圣,这或许是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影响所及,1475或许是南宋君主专制得到强化之后的必然结果。而真德秀走的是朱熹一路,力图以儒学使君王正心诚意,以此而达致外王之道,其名作《大学衍义》即是郑重上呈给宋理宗的,自宋以后大受重视,常被作为帝王经筵进讲的典籍,并被用来教育皇子。该书自谓“帝王为治之学,帝王为学之本”,共为四纲,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关于克段的议论在第八卷“格物致知”,卷末点题:“以上论天理人伦之正(长幼之序)”。真德秀既然以帝王之学为立言宗旨,就得说清楚帝王应该怎样处理兄弟关系——也就是说,单单批评郑庄公是不够的,还得告诉现任及以后的皇帝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怎么做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