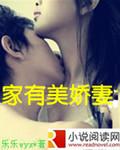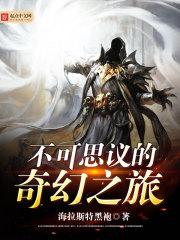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隐公元年注疏 > 第166章(第1页)
第166章(第1页)
庄公之心,以为亟治之则其恶未显,人必不服,缓治之则其恶已暴,人必无辞。其始不问者,盖将多叔段之罪而毙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恶日长,而庄公之恶与之俱长;叔段之罪日深,而庄公之罪与之俱深。人徒见庄公欲杀一叔段而已,吾独以谓封京之后,伐鄢之前,其处心积虑曷尝须臾而忘叔段哉?苟兴一念是杀一弟也,苟兴百念是杀百弟也,由初及末,其杀段之念殆不可千万计,是亦杀千万弟而不可计也。一人之身杀其同气至于千万而不可计,天所不覆,地所不载,翻四海之波亦不足以湔其恶矣。庄公之罪顾不大于叔段耶?
吾尝反复考之,然后知庄公之心,天下之至险也。祭仲之徒不识其机,反谏其都城过制,不知庄公正欲其过制;谏其厚将得众,不知庄公正欲其得众。是举朝之卿大夫皆堕其计中矣。郑之诗人不识其机,反刺其不胜其母以害其弟,不知庄公正欲得不胜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乱,不知庄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举国之人皆堕其计中矣。
举朝堕其计,举国堕其计,庄公之机心犹未已也。鲁隐公十一年,庄公封许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况能久有许乎?”其为此言,是庄公欲以欺天下也。鲁庄十六年,郑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则共叔有后于郑,旧矣。段之有后,是庄公欲以欺后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国,又欺天下,又欺后世。
噫嘻!岌岌乎险哉庄公之心欤!然将欲欺人,必先欺心。庄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虽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虽得志其心固已斫丧无余矣。在彼者所丧甚轻,在此者所丧甚重,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钓者之自吞钩饵,猎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讵至此乎?故吾始以为庄公为天下之至险,终以庄公为天下之至拙。
从文字技巧来看,吕祖谦这篇范文确实称得上范文。先从比喻入手,说明郑庄公如同钓者,叔段好比鱼儿,这世上没有人会因为鱼儿被钓上了钩而责怪鱼儿的不是。叔段原本并不坏,只是脑瓜笨,这才一步步上了庄公的当。然后词锋一转,加以道德评论,说叔段之恶与日俱增,而庄公之恶也随之与日俱增,人们都认为庄公只是杀了一个弟弟,作者却认为庄公动一下杀弟的念头就算杀弟一次,动了千万次念头自然要算是杀掉了千万个弟弟,罪过实在太大。
接下来再论郑庄公的用心,阴险至极,骗过了举国之人,处心积虑要除掉叔段。但这还不算完,作者又举《左传》后文的两处例子,以证郑庄公的欺世之心。最后一段峰回路转,说郑庄公虽然是加害人,自己却也是个受害者。这实在是一个怪论,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好奇,于是作者解释道:要想骗住别人,先得骗住自己的心,庄公得意于自己骗过的人很多很多,却没想到自己的心也同样被骗过很多很多。受了别人的欺骗,其害处无非只是身害;去骗了别人,自己却会落下心害。哀莫大于心死,心害甚于身害,欺人者本要欺骗别人,却也害了自己,好比钓者吞了自己投下的钩饵,好比猎人掉进了自己挖下的陷阱,天下只有最笨的人才会做这种事。所以说,郑庄公既是天下最阴险的人,也是天下最笨的人。
这番逻辑看似离奇,却是吕祖谦偏于象山心学的哲学观点的反映,所谓“人心皆有至理”,1493对“心”的伤害才是对人最大的伤害,这是对朱熹之“理”与陆九渊之“心”的巧妙弥合。
解经一路发展,从凿空之言到过苛之论,不一而足。当前人在某一点上做到极至之后,后人便容易从其他角度或其他立场来作一些翻案文章,非如此不足以出新。这大约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经学如此,其他领域亦然。如《东莱博议》论“介之推不言禄”,惊世骇俗地说道:“盗跖之风不足以误后世,而伯夷之风反可以误后世;鲁桓公之风不足以误后世,而季札之风反可以误后世”,其实这话倒也可以用到吕祖谦自己身上。一个社会里,如果道德标杆不切实际地树得太高,是不是“反可以误后世”?
吕的道德标杆可以说已经达到宗教标准了——庄公动一下杀弟的念头就算杀弟一次,动了千万次念头自然要算是杀掉了千万个弟弟,这就像《新约·马太福音》的逻辑:“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但和宗教不一样的是,神自然有能力洞悉人的内心世界,人又有多大可能隔着肚皮、隔着粗糙的史料、隔着千百年前的史官的眼睛、隔着千百年前辗转了不知几手的传闻来洞悉古人的内心?湛若水称吕祖谦“深诛其心术之微”,1494但无论他深诛得对与不对,都是无从证实的了。
要论诛心之重、发掘之深,似乎吕祖谦可以瞠乎其后,但事实远非这么乐观。比如我们还可以看看明代黄正宪的《春秋翼附》,把罪魁祸首跨过郑庄公而追溯到郑武公的头上,说他这个作父亲的当初没把事情处理好,这才给儿子们留下了致命的隐患。1495
这道理乍听上去实在令人吃惊,细想一下却也真有几分道理,可见对经义的发掘是没有止境的,像吕祖谦那样把加害者说成受害人也一样能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