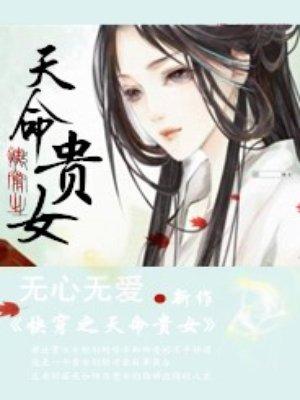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自指引擎论战 > 第23章(第2页)
第23章(第2页)
鲍比认真地问我。虽然不知道鲍比袜的脸在哪里,不过我这边姑且把脚跟一带认为是它的脸。
“要说蠢确实是蠢,不过要看怎么比较,所以请说明基准。”
鲍比没有理会我的反问。
“怎么说呢,你当场看穿了我是雄性。”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回答说自己不会被可爱的外表所迷惑,鲍比继续说:
“我这身打扮就是所谓的伪装。”
别误会,鲍比在这里用helvetica[18]强调说请多关照。我感觉到有危险,所以迅速点了好几下头。
“说到底,这是为了让对手疏忽大意的伪装,不过我们也不可能穿衣服,所以都是天生的伪装,是经过漫长的岁月淘汰之后获得的形态,越是显得可爱,越显示出检察官的优秀血统,越会为袜子社会所接受。”
明明没有问,鲍比却用飞快的语速解释起来。行了行了,我朝着它连连摆手。
“所以,看我这个样子觉得可爱,可爱也有程度的区别,这完全是人类尺度下的说法。请务必不要忘记,在袜子业界,这可是非常骄傲的雄姿。被伪装的姿态所欺骗,而受到嘲笑的,可是你们这些人类。”
我被它的气势压倒,更是用力点头不停。
“其实并不觉得羞耻什么的。”
鲍比用低沉的声音说。说实话,这个袜子的话题到底要发展到什么地方,我已经完全搞不清了。
鲍比和我,在几个瞬间的沉默里面面相觑。
我有种错觉,带蕾丝的可怜身姿,似乎在轻轻摇摆。
不知为何,鲍比开始的磕磕绊绊的解释,总结下来就是这样的内容:
就像不管有没有蕾丝花边,侧面有没有红色的缎带,鲍比都是源远流长的血统纯正的检察官一样,孩子穿的袜子,也不是袜子中的孩子。女性穿的袜子当然也不是袜子中的女性,老人穿的袜子也不是上了年纪的老兵。右边的是雌性,左边的是雄性,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是不存在的。
这个嘛,我想大概明白了吧。
“那么袜子的孩子在哪里呢,你当然会有这个疑问吧?”
鲍比郑重其事提出这个问题。我的回答非常简洁。
“没有。硬要说的话,丝线或者布头是孩子,缝纫机是父母吧。”
“缝纫机不做袜子。”
鲍比冷静地指出明显的常识。
“反正你们没有成长啊,世代更替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