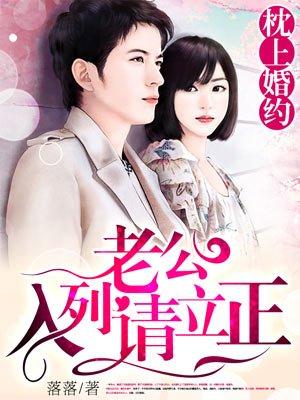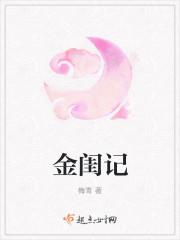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心理咨询室应具备的条件 > 于谦结婚磨刀霍霍(第1页)
于谦结婚磨刀霍霍(第1页)
“无妨,无妨。朕也知道,朕那汉王叔就是个没轻没重、不知所谓的性子。朕估计是他在边疆听闻此消息后太过兴奋,满脑子只想着要与你一同分享这份喜悦,以至于完全忘却了需将此事送至皇宫呈于御前。快些与朕讲讲,信里究竟说了什么?”
紧接着,我毕恭毕敬地将信件呈上,待朱瞻基阅毕后,又事无巨细地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郑亨家中时的所有分析。
“嗯,甚好。李爱卿果真不愧为历经沙场之人。此番剖析可谓鞭辟入里,深合朕意。朝堂之上能有像爱卿这样的股肱之臣辅佐,实乃朕之幸事,亦是我大明之福祉啊!”
我深知此时朱瞻基所言无非是随口夸誉几句,但仍故作惶恐之态道:“陛下谬赞了,微臣所为不过是分内之事而已,岂敢当此殊名。”
朱瞻基似乎非常满意于我此时表现出来的谦逊态度,他轻搓着双手取暖后,向我发问道:“依李爱卿所见,朕所拟之讨夷檄文何时才能传遍天下四方呢?”
“启奏陛下,只需静待时机成熟即可。待到失捏干一方尽显衰败之势、其内部新兴势力纷纷背叛并投奔瓦剌之际,便是我朝发布檄文整顿军队、准备出师征讨之时。”我恭敬地回答道。
接着,我与朱瞻基一同商议应给予鞑靼本部何种兵器增援之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们达成了共识——即将那些原本计划报废重铸的刀剑分批次有条不紊地运送至失捏干手中。这些虽属劣质品,但并非完全无法使用,只是稍欠顺手罢了;然而对于当前陷入困境的鞑靼来说,应该已足够应付一时之需。况且,说不定日后这些送出的兵器还会被用来攻击我方士兵呢!
方案既定,朱瞻基立即下令兵部、礼部和户部三方联手办妥此事。
诸事商议既定,朱瞻基蓦地望向我,沉声道:“李卿,你可晓得?杨溥自上次朝堂失利后,竟敢托病家居,久未上朝,此等行径,严重点可谓欺君之罪。你以为,朕当如何处置他?”
我略微思考了一番,心中暗自琢磨着:朱瞻基此刻似乎是真心诚意地向我请教问题,并无半点试探之意。想来或许是因为近日杨溥未曾上朝,使得整个文官集团都骚动不安起来。其中一些人恐怕认为杨浦此举无异于将皇帝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任由其被烈火煎熬。如此下去,难保不会有更多人心存侥幸,效仿此法以表达他们对朝廷和皇帝的不满情绪。
“陛下啊,微臣自幼追随太宗文皇帝左右,时常听闻他夸赞陛下乃是一位性情温顺、谦逊和蔼的翩翩少年郎。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尽管世事变迁,但微臣坚信陛下那温柔文雅、关怀备至的气度并未改变分毫。既是如此,杨大人自称抱恙需留家养病,陛下理当念及臣子之苦,予以体谅,允准他在家休养便是。”
朱瞻基一边摸了摸他那稀疏的胡渣,一边细细琢磨着我所说的话。慢慢的严肃的表情变得有了笑意。
“李卿,没想到你还是一个玲珑心呀,所言甚是!既然杨老大人想要在家将养,那朕怎么能让他带病上朝呢?来人啊,传朕口谕: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溥,夙夜为国操劳,如今重病而至,难以下榻。朕闻之心如刀绞,甚是痛心,着人赐予杨溥黄金百,绸缎百,仆五人,令其居家修养一载,待御医亲诊无碍之后再入朝议政。”
杨溥自以为抓住了朱瞻基的软肋,企图通过罢朝这种极端方式来逼迫其让步。然而,朱瞻基却并未如他所愿,不仅没有被吓唬住,反而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回击。
既然杨溥想让皇帝难堪,那么朱瞻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来一招釜底抽薪。杨溥不是称病不上朝吗?那好,就让他安心养病,何时能够康复上朝,则完全由御医决定。而这位御医,自然也是听从于朱瞻基的安排。可以想象,当杨浦得知这个消息后,必然会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他恐怕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精心策划的计谋竟然适得其反,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至此,杨浦逐渐退出了朝堂的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杨士奇也明确表态,绝不会阻挠北征之事。如此一来,只剩下杨荣一人对这些事情漠不关心。此刻,杨荣的首要任务乃是悉心教导宫中的诸位皇子。
而且他本人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默默无闻、低调行事。除了在朱棣登基称帝之前,曾经半路拦截朱棣,并质问他:“先去祭拜皇陵呢?还是先举行即位大典呢?”——这算是他唯一的一次高光时刻之外,其他时候都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表现。尽管他其实深藏不露、实力高深莫测,但从来不曾与他人产生过直接的冲突和矛盾。
因此,现在将杨溥废除之后,朝廷上剩余的文官们即使再怎么折腾,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来。毕竟,三位内阁大臣之中,一个被排挤在外,一个对世事漠不关心,还有一个已经答应不会加以阻挠。如此一来,北伐之事已然成为定局!
我在从皇宫返家的途中,心情愉悦至极,不禁一路兴奋地哼唱着歌曲。这便是所谓的因果报应啊!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想到当初备受欺压的我,如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时候!
时光荏苒,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流逝而过。转眼间,时间已来到八月中旬。在这段日子里,整个朝堂一片宁静祥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喧闹嘈杂、混乱不堪,甚至连整个京城都显得格外平静。仿佛一切都陷入了一种死寂般的氛围之中。
而在这期间唯一在死水潭里建起一朵水花的,则是于谦低调的迎娶了朱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