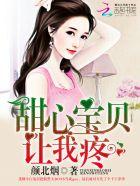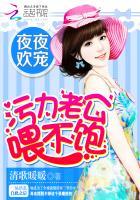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明朝皇权 > 第32章(第1页)
第32章(第1页)
久已厌倦政治的顾宪成,退出&ldo;江湖&rdo;,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出面为挚友李三才辨白。他写信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说:&ldo;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rdo;,希望叶向高、孙丕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还李三才一个清白。这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谈不上&ldo;遥执朝政&rdo;。不料这些信件被刊登上邸报(政府公报),引起轩然大波。那些攻击李三才&ldo;结党&rdo;的官僚,以为抓住了把柄--东林书院&ldo;遥执朝政&rdo;。
这是顾宪成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他对李三才从相识到相知,对他的人品操守十分敬仰。万历三十七年他在信中对李三才说,现在时局千难万难,只有才干卓识如你这样的人,&ldo;方有旋转之望&rdo;这是促使他写信给阁部大僚的缘由。当然他也深知,由他这个在野的革职官员来议论此事,必然会遭到嫌疑。事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钦佩李三才每当&ldo;风波汹涌之时,毅然出而挺身担荷&rdo;,&ldo;不肖独何心而忍默默&rdo;!虽然他的言论必然会遭来麻烦,但他坦然得很,&ldo;聊以尽此一念而已&rdo;。
顾宪成这位桃花源中人实在是太书生气了。以前在朝时他就特立独行,如今在野了,依然对政治斗争的险恶估计过低。事态愈来愈扩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愈来愈厉害。这时他才意识到写这些信是失策的,在给朋友的信中无可奈何的说:&ldo;去岁救李淮抚(指李三才)书,委是出位&rdo;,为此深深悔恨;又说:&ldo;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rdo;
然而为时已晚。政治斗争的险恶难以逆料,不但李三才陷入了危机,而且顾宪成与东林书院也受到牵连,一些别有用心者,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ldo;东林党&rdo;。始作俑者便是徐兆魁之流,他无中生有地说:&ldo;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rdo;,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以至于此。
万历四十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
顾宪成之死,触发正直人士为他辩护洗刷的激情,户部广东司主事李朴大声疾呼:&ldo;顾宪成也,久栖林壑,游心性命,即一书出而议及时事,可从则从,不可从则止,有何长鞭足以制人?乃满朝之人哄然四起,宛如敌国,不为&lso;遥制国是&rso;,则为&lso;不肖渊薮&rso;,且并讲学而非芍之。&rdo;然而毕竟寡不敌众,李朴被整得狼狈不堪,落得个&ldo;调闲散用&rdo;的处分。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愈演愈烈,污蔑它是&ldo;遥制国是&rdo;的&ldo;党&rdo;。御史田一甲甚至说,东林书院&ldo;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rdo;,&ldo;门户之威炽矣&rdo;,&ldo;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赞、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rdo;云云。不但视东林书院为&ldo;党&rdo;,而且还扯上&ldo;入党&rdo;、&ldo;不入党&rdo;的组织关系,荒唐之极。顾宪成何时&ldo;建党&rdo;?李三才等何时&ldo;入党&rdo;?莫名其妙。
把以讲学为宗旨的东林书院看作一个&ldo;党&rdo;,无异于重现南宋时禁锢朱熹办书院讲学的&ldo;伪学逆党&rdo;之禁。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在奏疏中点明了这一点:&ldo;今为世道计,不患讲学,患不讲学;又不患不讲学,患不真讲学&rdo;:&ldo;且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rdo;。他忧心忡忡地指出:&ldo;伪学之禁网益密,宋之国祚亦不振&rdo;,提醒当权者深长思。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时期,对东林书院近的迫害变本加厉。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仿照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座次与诨号,编了《东林点将录》,公然把李三才列为&ldo;东林党&rdo;的第一号人物--相当于梁山泊的晁盖,其全称是:&ldo;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rdo;,开列了108人物的黑名单,把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都网罗在内,一一予以镇压,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天启五年(1625年),由政府出面,捣毁了东林书院。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毁于政权的暴力,令人唏嘘不已。
&ldo;大刀手&rdo;杨琏
古代有这样一句民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反映了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世哲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者,往往死得很惨;趋炎附势,善于拍马溜须者,往往飞黄腾达。于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向上爬,学会了明哲保身,曲阿附世,不敢讲真话,假话套话连绵不绝,身上弥漫了乡愿气息,官场风气由此腐败不堪。然而中国的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一向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乡愿如仇雠。因此,&ldo;直如弦,死道边&rdo;的官僚,代不乏人,成为历史的亮色。
杨涟就是其中之一。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出任常熟知县,被举荐为&ldo;廉吏第一&rdo;,升户科给事中,转兵科给事中,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泰昌、天启两朝以敢于直言极谏,抨击恶势力,而闻名于政坛,《明史》称赞他&ldo;为人磊落,负奇节&rdo;。这七个字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在泰昌、天启两朝的&ldo;红丸案&rdo;和&ldo;移宫案&rdo;中,把个人功名利禄与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挺身站在风口浪尖,力挽狂澜。他的最为彪炳于史册的事迹,是上疏弹劾权势显赫的&ldo;九千九百岁&rdo;魏忠贤,结果遭到杀身之祸,并且被&ldo;阉党&rdo;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排在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天间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等人之后,给他的名目是:天勇星大刀手左都御史杨涟,在他后面的是: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题目中&ldo;大刀手&rdo;三字的出典就在于此,显现出&ldo;阉党&rdo;心目中杨涟的厉害--似乎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ldo;大刀手&rdo;,列位看官千万别误会,以为杨涟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入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