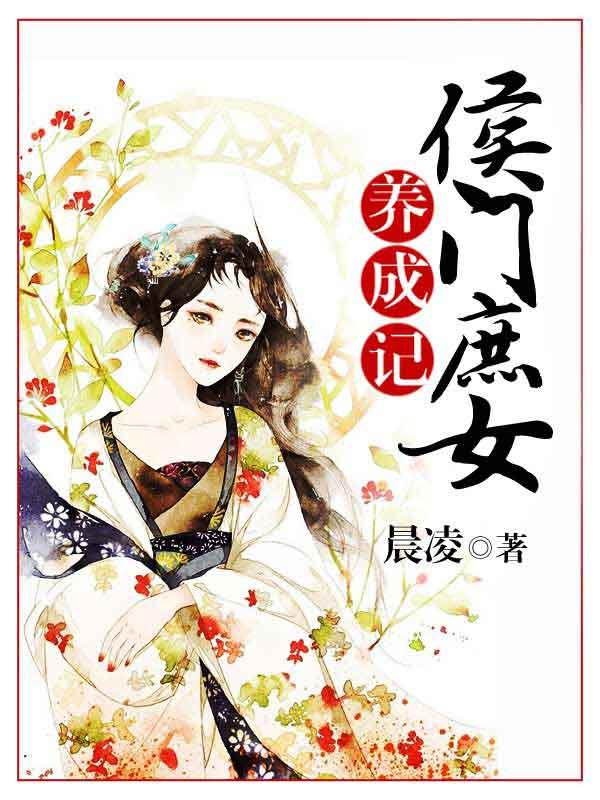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公主的野望讲了什么 > 第95节(第2页)
第95节(第2页)
&esp;&esp;姬萦是怎么也不可能让他咬去一半肥肉的,徐籍要分她的羹,这倒也罢了,徐见敏是个什么东西,也想从她碗里抢食?
&esp;&esp;“姬萦,你是想抗命不成?!”徐见敏耐心耗尽,一拍石桌,露出真实面目。
&esp;&esp;姬萦退出石凳,拱手垂首称不敢。
&esp;&esp;徐见敏瞪着不知是被酒精还是愤怒染红的眼睛,恼怒不已地看着姬萦。
&esp;&esp;寂静的僵持之中,告里清冷的声音缓缓响起。
&esp;&esp;“敏郎,州牧府是要搬去兰州吗?”
&esp;&esp;告里冷不丁地一句打岔,让徐见敏脸上的怒色被疑惑取代。
&esp;&esp;“你怎么会这么说?”
&esp;&esp;“我听这位大人说,暮州的官俸和兵饷都已拖欠多年,以致人心不稳,军心动荡。我心里好生害怕。”告里垂下眼,右手轻轻放在她微有突起的小腹上,“眼下好不容易有银两填补之前的亏空,让暮州安定下来,大人却要抽走一半去兰州,所以我才有这样一问。”
&esp;&esp;“州牧府自然不会轻易变动的,而且你是女人家——你不明白钱张严曹四家到底有多少底蕴,哪怕暮州只留一半,发清此前的欠款也是绰绰有余。”徐见敏说。
&esp;&esp;“以前的发清了,以后的就不发了吗?”告里幽幽问。
&esp;&esp;徐见敏被她问住,愣了一下。
&esp;&esp;姬萦适时开口道:
&esp;&esp;“正如夫人所说,暮州此前的欠款只是花销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如何振兴民生萧条的暮州,使百姓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真正有牧治所的样子。这些,都离不开银子。”
&esp;&esp;“事有轻重缓急,下官理解大人作为暮兰两州父母官的心情,但暮州作为牧治所,理应是
&esp;&esp;走出宰相府后,姬萦骑马回到太守府,向府内等待结果的众人报了平安后,又从后院的角门溜了出去,穿各种小巷,走最短距离去官驿。
&esp;&esp;路上下起了濛濛细雨,清新的雨滴扑面而来,姬萦更觉心情爽朗。
&esp;&esp;到了官驿,她将马拴在门前木柱上,抹去头顶雨滴,高高兴兴地径直而入。
&esp;&esp;敲开徐夙隐所住的厢房后,姬萦只见到了水叔。
&esp;&esp;她开口就问:“水叔,夙隐兄呢?”
&esp;&esp;水叔正拿着一张手巾擦拭厢房窗框上的灰尘,不冷不热地瞥了姬萦一眼,说:“公子出去了。”
&esp;&esp;“没让你跟着?”姬萦惊讶道。
&esp;&esp;“公子不让我跟着。”水叔没好气道。
&esp;&esp;见不到徐夙隐,姬萦在这里久留也没意思,她正要告辞,水叔放下手巾,忽然说道:
&esp;&esp;“但我知道公子去做什么了。”
&esp;&esp;姬萦用好奇的目光等着他继续说完。
&esp;&esp;“公子猜到你此去必会喜色而归,已提前去准备查抄清单了。公子是宰相派来的监察使,由他拿出的清单,徐见敏不得不信。公子为你,苦心费尽。”水叔似乎强忍着什么,戛然而止了半晌,才又缓缓说道,“以前的事,公子不想提,老夫便不提。只是希望姑娘,往后莫要辜负我们公子的殷殷情义。”
&esp;&esp;姬萦一愣,然后笑了起来。
&esp;&esp;“水叔放心,夙隐兄身份高贵,却愿意助我成就霸业。此情此意,姬萦铭记于心,即便水叔没有今天这番话,我也绝不会辜负夙隐兄的深情厚谊。”
&esp;&esp;水叔瞪着她,只见眼前这年轻姣美,言笑晏晏的女子,左脸一个世字,右脸一个美字,额头上再赫然一个姬字,端的是可恶至极!
&esp;&esp;他话都说到这地步了,她竟然还在装傻卖乖!
&esp;&esp;他一口气噎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最后化为一声重重的哼声,扭过头去继续擦拭窗框,不再搭理姬萦。
&esp;&esp;这老头古里古怪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姬萦毫不在意他那副噎气的表情,神情自若地告辞后,站在官驿的屋檐下,看着外边细雨霏霏的雨幕,想了想,找官驿的伙计“借”了一把伞。
&esp;&esp;那老伙计认出她是本地太守,根本不敢收钱,姬萦还是按市价给了他几个铜板。
&esp;&esp;在感恩戴德的老伙计的目送之下,姬萦把油纸伞夹在腋下,灵巧地跨上马背,骑马往州库赶去。
&esp;&esp;徐夙隐出门得早,肯定没有带伞,姬萦这把伞,就是给他准备的。
&esp;&esp;姬萦自己,那可是别说淋雨了,就是在河里泡两天两夜,也不定会生病的铁一样的身体!
&esp;&esp;就在她兴冲冲赶往州库的路上,雨突然大了。原本像银丝一样的细雨,化为瓢泼的大雨,淅淅沥沥砸在人间。
&esp;&esp;姬萦不得不展开那把为徐夙隐准备的伞,遮挡在自己头上。
&esp;&esp;急赶慢赶到了州库大门,姬萦一眼就看到正在将许多红木箱子急急忙忙往室内搬的衙役们。她没见到徐夙隐的身影,跳下马来,拦住站在屋檐下监督的荣璞瑜,故作不知道:“你们这是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