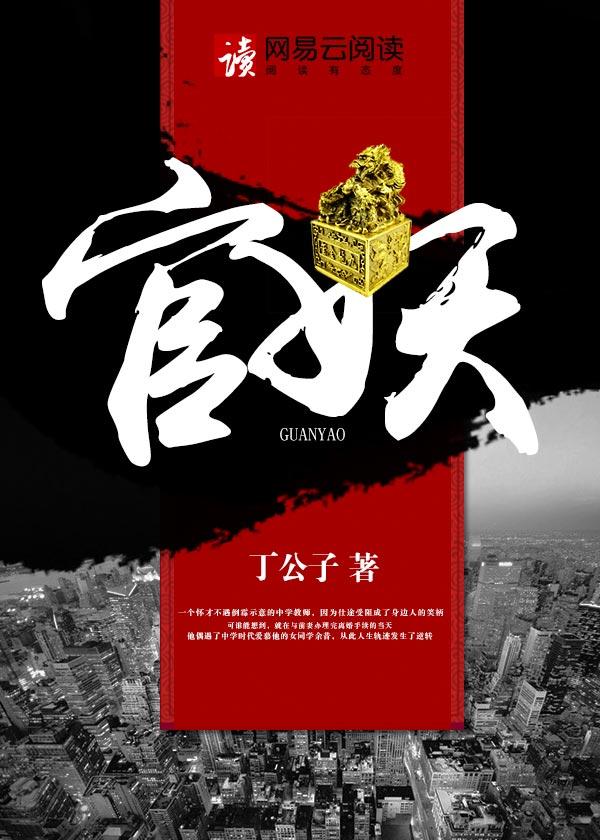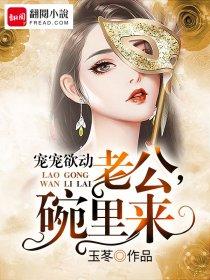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曾国藩当官 >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第1页)
曾国藩主意已定,随手便把帖子放过一边,仿佛放下一桩心事。他到茶房那里要了半盆热水,要用热水搓一搓因抄写过度已经肿起老高的右手腕子。右手腕子如不及时活血化淤,他第二天就别想稳稳地握笔了。‐‐不办公事,赵楫不把他告到文庆那里才怪!
哪知道,不经热水搓,手腕疼痛尚能忍受,热搓之后,许是血液散开的缘故,倒大疼大痛起来。
他不得不让茶房打着灯笼到对面的药铺买了贴止痛膏药贴上,这才略有缓解。
曾国藩越想越气,已经躺到床上歇息,又披衣爬起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提笔在一张八行纸上,刷刷点点写了个告示。
告示云:曾国藩出身贫寒,长相不雅,箱内无银,虽任检讨一职,却是七品小官,俸禄有限,除衣食住行,已无赢余,即日始,凡京官上宪、同僚坐席陪酒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请帖亦不收存。见谅。
这张告示被他一早便方方正正地贴到会馆的柱子上。
不久,曾国藩因&ldo;办事糊涂,办差敷衍&rdo;,遭到御史参奏,被道光革去翰林院检讨实缺,成了翰林院候补检讨。每日虽也照常去翰林院点卯,却没了实际差事,没了俸禄,境况竟不如庶吉士。依礼向赵楫等上宪请安、道乏时,这些人不仅把脸扬起老高,嘴里还总时不时地冒出一二句嘲讽、讥笑的话来。曾国藩几次被弄得尴尬万分。以往的同僚、同乡,有几个与他很是不错的,此时也不知是怕丢了自家头上的乌纱帽,还是怕上宪怪罪,影响自己的前程,竟然也开始躲他。他有时想凑过去说句话,这些人不是推托公事忙,就是找个理由走开,分明是不想理睬他。
苦闷、孤独中,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今日今时吾在兹,我兄我弟倘相思。
微官冷似支麻石,去国情为失乳儿。
见惯浮云浑欲语,漫成讨句末须奇。
经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成百不知。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他用毛边纸装订了几个本子,给自己订了一年的&ldo;日课册&rdo;,决定&ldo;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rdo;。日课册被他命名曰《过隙影》。《过隙影》其实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看的日记:&ldo;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rdo;,备&ldo;念念欲改过自新&rdo;,以求进取。
无缺份、无俸禄、无同乡、无朋友的这个&ldo;四无&rdo;期间,他只能自己和自己讲话。
让他想不到的是,一日一篇的《过隙影》,竟使他成癖成瘾,再难割舍。
曾国藩的遭遇也同时激起了部分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职位的官员的不满。这些人虽不在翰林院供职,但讲起话来,还是有些分量的。
著名国学大师,官居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唐鉴先生,当时对曾国藩道:&ldo;涤生做此常人不敢做之事,实国家之幸!‐‐老夫当寻机会在皇上面前为汝开释。&rdo;
倭仁、吴廷栋等唐鉴的一班弟子、老友,也在人前人后为曾国藩鸣不平。
曾国藩心稍慰。
皇家寺院里的钟声悠远而漫长,一年一度的国庆大典(皇太后寿辰)就在这样的钟声里开场了。
依道光帝的意思,今年的国庆还和往年一样,在京的官员每人赏一碗面条,给有功的督、抚们赏上两件黄马褂,武将们中优秀的赏个&ldo;巴图鲁&rdo;算了,但大学士穆彰阿却认为不妥。
穆彰阿郑重其事地上折子说:&ldo;皇上自登基以来,无日不操心费神,勤俭克己,更是超过列祖列宗。今年是皇太后七十寿辰大典,非盛世不能相逢,非明君不能遇到。我天朝圣国的国庆非小夷小邦可比,岂能一碗面条了事?尤其是战乱之后,为向小夷小邦显我天朝强大,大典非隆重不能震慑。只有这样,国太才能心安,夷人才不敢正瞧我天朝。&rdo;
驻藏大臣琦善琦大人,也从边疆发来折子,极力怂恿皇上轰轰烈烈地举行国庆,并且强调说,悄悄地过国庆,虽有了节俭之名,却也算示弱于外夷了,举国上下都无光。
道光帝拗不过大臣们的苦劝,只好勉强同意,但还是告诫承办大典事宜的顺天府:&ldo;凡事能俭就俭,断不可勉强。&rdo;
顺天府正三品府尹一连叩了八个响头,一连说了八句&ldo;臣一定遵旨办理&rdo;,这才喜滋滋地退出。
于是,大典的前奏曲便在顺天府的操持下开始了。
先是清理临街店铺的招牌。
顺天府工部办事房规定:&ldo;凡京师店铺招牌,限五日内一律到城南李记招牌铺统一样式,统通更新换好,不许到其他招牌铺制做。有违抗者,轻者封锁铺子,重者罚银入狱,无论铺面大小,概莫能免。&rdo;
规定里所谓的李记招牌铺,就是顺天府工部衙门张尚书的老泰山和大清国工部衙门匡侍郎的小内兄合开的专为商家制做招牌的铺子。
据说,仅皇太后这一次生日,&ldo;李记&rdo;就把钱挣海了。‐‐就算李记招牌铺十年不接生意,也倒闭不了。
此规定当天即张贴出去,五日后便派员一条街一条巷地验视,好不认真。
有几家自认为招牌是新做的,只是样式有违,想蒙混过关,店主便被捕快锁拿,费了上千两的银子赎罪不说,还照样把旧招牌砸碎,到&ldo;李记&rdo;做上个新的,这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