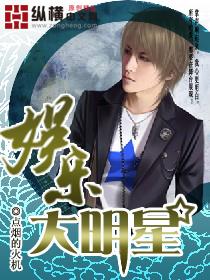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探金草百度百科 > 第54章(第1页)
第54章(第1页)
史可法又瞅了一眼,六头牛、四十石的大车,上面七八桶,送到现在,大半该都是空桶了,四个送酒的伙计,拿木担拴绳套着,抬了一桶满的,吭哧吭哧地进了勾栏。
勾栏买锅烧是对付武官用,一般都兑水,所以不买整桶,在里头要先接酒,再计分量,费工夫。
就算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也得快,史可法左右手各搂一人,一使力,不打晃地从胡同出来,两步就到了酒车旁,把人扔到车上,开了酒桶盖子,一股烧锅味直冲鼻子,那都是齐胸前高、拿铁箍勒着的重木桶子,比水缸还大了半圈,一人一桶,装得恰好,待把三人都塞在桶里,盖好盖子,也不过一眨眼工夫。
这一晚,真算没白折腾。
史可法长舒一口气,三人都被勒闭了大脉,没两个时辰难醒,又被塞紧在装烈酒的桶里,被酒气熏着喘气,妥帖地会大醉一场,两场晕摞在一起,没到天亮醒不来。这牛车慢,拉到大兴,少了也得半宿,即便路上醒了,再赶回来,也是天亮,自己的事,早也办完了。
只是自己今天一下露了能耐,再往后,就麻烦了。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三人一走,这一晚就没了跟着的鬼,该找的人,也能找了。
徽商的宅子,都在西四的几个胡同里,史可法一步都没闲着,一路快跑,眼睛耳朵盯着四面八方,那真是全北京现在最快的两条腿,转眼就到了。
先到了徽商领头的李顺城家,这人是做粮号的,老师治水后,他家生意千顺百顺,现在是安徽有名的大粮号,算是承老师恩最多的,对老师奉若神明,救老师这事,也由他来联络众商号,那日在教坊司和谢启光接头的,也是他。
这时候到了亥时,不敢在夜里敲门,敲了怕也不给开。索性直接进去,史可法蹬墙上房,先打量四周,明月高悬,天晴如雪,猫腰看了好一阵子,四周没见着听着锦衣卫的动静,才定睛看李顺城家。
这一看,心都拧了个疙瘩,整个院子,没一间房亮着灯,跟死了一般,丁点人气儿没有。
跑了?或是睡下了?
翻身下了院子,脚下是灶房,家有没有人,摸灶就知道,进去一打听,没烟火味,也没饭味,再一摸灶,凉的。
心咔嚓也凉了,真的跑了?
转身就出去奔厅房,这院子不小,几进几出,里头外头找遍,哪有一个人!
跑了,是真跑了,可悔出了血,那晚就不该放他们回家,就该留着他们。
再去其他家看看,又翻身上墙,连去了几家,都是黑灯、凉灶、空房,终于在第六家逮着了个守房的老头,老头被吓了个半死,话都说不利落。
“走了,走了好几天了。”
“说去哪儿了没有?”
“没。”
“再好好想想。”
“爷,是真没,走得失魂落魄的,好多东西都没拿,我们下人谁敢问哪!”
“留下什么话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