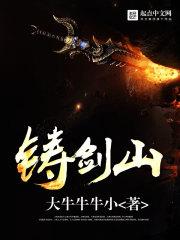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料青山如是 > 第102章(第2页)
第102章(第2页)
掉了皮的马甲强行披上,终归是不伦不类的。
沈青也没有再使用这个马甲的念头,但出于对自己作品的谨慎,她还是最后一次登上了马甲号,把自己已经发表在这里的文章诗歌都一一记录下来。
记录时,感叹于自己以前随手写的关于安山的一些小诗。
十几行字,简单描绘安山的一道弯的特色。总共写了□□首,地点不同,季节也不尽相同。
“我想看到素白的绸缎,偏偏找我的却是葛衣。江南的柔情消失在了这个冬季,夏日的粗粝却铺在了整座山里。”
这是她上个冬季,数月盼雪而不得,所写下的几句牢骚话。
当时觉得只是信手之作,如今看到,却觉得写得还算不错。
另外几首,差不多也是这种风格,长长短短,写安山,也写她想象的安山。
她用电脑文档把诗整理了一下,再用打印机打印了出来。
看着电子屏幕读诗,和看着白纸上的文字读诗,味道是会不一样的。
她看着亲生的这些小诗们一首首“跃然纸上”,自己的心情也变得很好,翻页,注划,一首首看过去。
“真的蛮不错的。”她自我评价。
山和诗,好像从古至今都是绝配。无数的诗人为山写诗,也有无数的山为诗人成山。
李白看遍天下名山,眼骨发酸。于是他说,这里该是一座让我看不厌的山。随后众鸟忽得高飞而起,孤云悠哉地在天中独去。敬亭山从天而降,落到一个仙人的面前。
仙人以所见入诗,诗又以所写成仙。
安山之上,自然也留下了不少的千古绝句。
生活在这里的人,无论有文化与否,都会背上两句。
沈青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从安山剽窃来秀丽,填充进自己的诗句中。
她把打印出来的小诗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晚上李岩送货上来,顺道吃晚饭的时候,就看见了这几张叠在一起的纸。
沈青说:“我自己写的。”
李岩拿起来看,问她:“我能看吗?”
“当然。”
于是他仔细地读了两首。
沈青的文字很干净,很简洁。她很少用华丽的修饰词,但文字中的灵气却遮掩不住。
即使李岩并没有品鉴小诗的经验,但他也很喜欢其中感觉。
“写的是安山?”
“嗯。”
“写得好美。”他说。
沈青凑过来看他拿着的那首诗。这是这几首里头最长的,一共十八行。诗中描绘了一个旅人从山脚到山顶的一路见闻。
沈青道:“安山本来就很美。哪一个人会不爱安山一路的风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