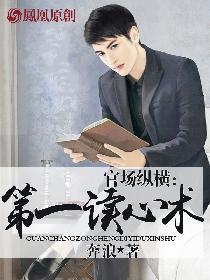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成婚五年后贤妻失忆了免费阅读最新 > 分卷阅读63(第1页)
分卷阅读63(第1页)
度上山去瞧兰夫人,兰夫人已经醒了,正倚靠着床榻喝药,神情一片病怏怏。
见着她来,兰夫人眸中一亮,挣扎着想起身,宁臻和赶忙上前扶着她:“夫人,可无事?”
二人脖子间具是一片青紫,兰夫人握着她的手:“你……为何会来,若非你,我早已没了性命,请受兰盈一拜。”
宁臻和赶忙扶起她:“夫人不必如此,我本就是受卫贤意卫二姐来寻您,想同您学习绒花的技法,结果恰好遇上了这事,说明我同您有缘。”
“原是如此,就算没有贤意的介绍,你放心,我也定当倾囊相授。”
得了这句话,宁臻和露出了个欢欣的笑意,颊边漾起浅浅的梨涡,连脖子上的伤口都不怎么疼了。
他们约定好兰夫人伤好便开始教学,刚回府,她就被从州叫住:“夫人,大人叫您去一趟巡检司,说是犯人缉拿,叫您去认认人。”
“知道了。”宁臻和听闻犯人已被缉拿,本能想起昨日之事,心头有些惴惴。
巡
检司的牢狱内,晏仲蘅站在牢门前,黑色的披风衬得他高大挺拔,侧脸锋锐,待狱卒说夫人来时,他脸色骤然柔和了下来。
“臻臻。”
宁臻和避开了他的视线,看向牢狱内的那人,随即惊愕的瞪大了眼睛:“这……这不是……”
“是,你看他胳膊上的伤口,可熟悉?”
狱中之人尚且体面,晏仲蘅未曾用膳,宁臻和视线落在了他被扒开的伤口上,凝视了些许,笃定:“就是他。”她话语还微微有些颤抖。
晏仲蘅心口蓦地一疼,下意识揽住了她的肩头:“臻臻……”
宁臻和还是泄了些后怕,直到出了牢狱浑身的沉坠还未散去,她回过意识后发觉晏仲蘅始终伴在他身侧:“我……我那日在桃林听到了他和贤二姐的谈话。”
晏仲蘅揽着她的手未松开,神色凝着:“什么话……”
宁臻和没发现他的手,认真回想了那日随后告诉了他。
“我知道了,此事你莫要再插手。”他替她系紧了斗篷,轻声道。
宁臻和有些不自在,后退一步晏仲蘅的手落了空,他默了默:“待过些时日随我一起回京。”
宁臻和顿时冷下了脸色:“我何时说要回京了。”
“我说的是过些时日,足够你把想做的事做完。”晏仲蘅早就得知她的心思,自然也是满心支持,但是她必须同自己回京城,在这一点上晏仲蘅始终不放心。
“那我又凭什么听你的安排。”宁臻和转头就走,对他总是试图掌控自己烦的要死。
晏仲蘅老毛病又犯了,他吃软不吃硬,若是有人硬要来,那他则会比对方更硬,若是对方率先软下来,他才会允许做出底线之外的事。
恰好宁臻和性格还未被驯化,自然不会愿意同他周旋,他冷着脸跟在她身侧,心头的火气覆盖了他的理智。
“长顾快要去流放之地了。”一句话,磨灭了她的骨头。
“去哪儿?”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晏仲蘅深深的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宁臻和却懂了,想起了那日的敲打,去哪儿都是他略施手段,她顺,弟弟去的地方好,她逆,弟弟去的地方差,说不准连命都保不住。
他们的如今,何尝又不是利益交换呢。
宁臻和有些无力,揉了揉脸颊:“知道了,都按你说的办就好。”
虽达到目的,但晏仲蘅并没有开心多少,他想要的不过是妻子能听话些,像以前一样,竟如此困难,可以说他拿十六岁心性的臻臻有些毫无办法了,只能被迫拿此手段。
那些对晏老夫人说过的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