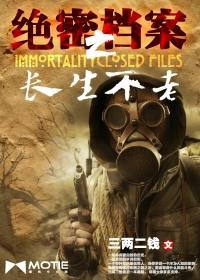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锄禾日当午的意思 > 106越描越黑(第1页)
106越描越黑(第1页)
田小午安静的坐在门槛上,周遭人声鼎沸,众人的欢喜乐笑阵阵传来,对锄头这段风流韵事的羡慕调笑不绝于耳,那些让人面红耳赤的话一段段的飘进田小午耳朵里,组合成一出出□荡漾的三级剧,一幕幕的闪过小午的脑海里,竟是比亲眼所见都**香艳几分。
她一直这么紧咬着下唇盯着篱笆门,脑子空空如野,半晌,她才站起来,并不理会那些个为着锄头的亲事忙里忙外的众人,自顾自的去厨房刷锅烧火去了,又见她虽是不喜不笑,却是手上的活计分毫不乱,做事井井有条,大伙儿以为她姑娘家的小脾气使性子已经闹过去了,也不去管她。
田小午在那个她熟悉的灶房里偷得这片刻的清净,杂乱的心绪平复了许多,也慢慢找回刚刚散乱的理智,从众人的七嘴八舌里抽丝剥茧般理顺了锄头这桩亲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无非就是在她不在的这些时日里,锄头跟那王黑妹眉来眼去,情根暗许,接着便是趁着这郎情妾意加上年少气盛来了几场月夜相会,**间自然好事已成,天当被地当床做了对交颈鸳鸯,又好巧不巧的被撞见那□相拥的风流形状,这段私定终身的风流韵事终于大白于天下,此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那王家老儿见事已至此,又是自家姑娘心甘情愿,且自家闺女已是坏了名声,除了锄头已是别无选择,又恐夜长梦多,不得已便是顺水推舟差人提亲,白送了锄头一个便宜媳妇。
过程虽是跌宕起伏,却也是合情合理,连田小午都几乎信以为真,觉得这情节严丝密扣,找不出什么杜撰的痕迹,可是,田小午恢复清明后却坚定的告诉自己,三人成虎,不由的你不信,但故事就是故事!
或许锄头娶王黑妹这事的确是砧板上的钉,但这个两情相悦互许终身的戏码,也只能是听听而已,因为那男主角是锄头,他或许未必喜欢自己,但是那一夜他对自己做出过那种事,要让他不负责任的这么快就移情别恋,再去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卿卿我我根本就不可能。
即使锄头如一般男人一样也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他也不可能换位思考的那么快!田小午恶狠狠地想。
她在心里说服着自己,给自己撑到锄头回来的勇气,即使这事是真的,她跟锄头那刚刚开始萌芽的感情要就此夭折,她也要等着锄头亲口告诉自己。
可是,锄头走丈人家这一趟实在是去的太久,久到日落西山,大伙儿已是帮满将锄头的破屋子都基本收拾停妥,只等着后面采买用具布置新房了,他还是迟迟未归。
虽是那颗七上八下的心在这滚锅油里煎熬了一下午,但待客之道田小午还是懂的,她还是就着家里拿得出的菜色倾尽所能的准备了几碟子下酒菜,蒸好了一大锅的玉米面饼子,林林总总的摆满了一桌子,就等着锄头回来了。
就在大伙儿都在嘻嘻哈哈哈七嘴八舌的议论,锄头跟那王黑妹是不是甜的蜜里调油,舍不得娇滴滴的小美人,今夜直接留宿王家的时候,锄头心急火燎的喘着粗气一头是汗的跑了进来。
见到一院子的人他明显一惊,又看到大伙儿手里的明显是为他成亲准备的活路更是眉头紧皱,声音略带嘶哑的问道:“张婶子,你们这是干啥呢?小午呢?我去柳家庄子找她,人家说她回来了,她人呢?小午——”
“不是说你要挑个好日子娶亲了吗?这不是大伙儿子来帮你准备准备,不然你这里啥东西没有,仓仓促促的你娶的什么媳妇?”
“我要娶亲?谁说的?没有的事儿,小午呢?”锄头听的大家伙儿这么说更是心急如焚,目光穿过人群到处找着田小午。
田小午在灶房里已是听见锄头满院子喊她的声音,不知为何,只是这么一声急切的呼唤,她心里那份不安慌乱的潮起潮涌已然瞬间平静。
他那么在乎她,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感情怎么可能那么不堪一击?
田小午理理心情,有些心疼的端着一碗茶水赶忙朝锄头走去。
猛然看见田小午端着茶过来,锄头已是顾不得接过她手里的茶碗,立即一把抓住她的手,焦急的解释:“小午!这种没根没影的事儿你可千万别信啊!”
“什么是没根没影的事儿?这还成了我们多事了?这媒婆不是早上来过了?树生说人家媒婆说了让你这几日尽快下聘择日就成亲不是?媒婆前脚才走你不是后脚就赶着去王家商量成亲的事儿了?婶子不是还听说你要去问问那王家闺女说是想要啥不是?婶子怕你一个人也没个长辈给你操心张罗,这不就叫着这些个父老乡亲、小伙儿劳力的先帮你制备帮衬着点,不然日子都定了还空的跟寒窑似的,用啥没啥,你还成啥亲?你等着抓瞎吧!”一片好心锄头竟然这么不领情,好像还是他们多事了一般,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的张大婶当下面色不悦道。
“张婶,你先别气,锄头哥,你也别急,先喝口水润润嗓子,有事慢慢说,趁着大伙儿都在,你细细的将这些来龙去脉说清楚。”田小午走进才看清了锄头那风尘仆仆、嘴唇干裂的样子,赶忙将水递过去。
锄头此时却是顾不得喝一口,急着澄清说:“唉!婶子,你,你,你们想到哪里去了?我几时说过要娶那王家闺女了?媒婆是来了,我是去她家了,可不是去商量这个什么劳什子亲事,而是去质问,那王黑妹这么摆俺一出,到底是为啥,她到底想要干啥!”
“什么?你不娶人家?还问人家要干啥?人家自然是要你负起男爷们的责任,堂堂正正娶人家进门呗!你小子都把人家闺女给睡了,你现在竟说不娶人家?你小子良心被狗吃了吧?啊?锄头,咱们老爷么顶天立地,可不能干这吃干抹净擦嘴赖账的混蛋事啊!”
心直口快的二蛋听了锄头的话火冒三丈,当下便为王黑妹抱不平。
“二蛋,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听谁说的?俺锄头啥时候睡过那王黑妹?”锄头又气又急,脸红到脖子根了。
“嗨!你小子还不认账?现在渡头上都传遍了,人家王黑妹都默认了,人家一姑娘家还能无中生有拿自己的名声抹黑不成?且你跟她那段子事,鸭蛋可是亲眼看见的,这你都想赖?”
“那晚上鸭蛋看见的那儿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也不知道王黑妹为啥就,就承认,可我是真的没做过!我跟她清清白白,啥事都没有!”二蛋说的有板有眼,锄头急青筋直冒。“清清白白?那晚上鸭蛋看见的光着上身抱着人家姑娘的是你小子不?”二蛋不依不饶。
“是我,可——”锄头窘迫的看着小午的脸色,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你可啥啊可,鸭蛋还说了,夜里黑虽是看不真切,可那王黑妹躲在你衣裳里面半露着一身白肉,却是瞧的清清楚楚的,刚刚当着小午妹子的面,我都没好意思说,空穴岂会来风?你还死鸭子嘴硬说是跟人家清清白白啥事都没有!这都清白?那你告诉兄弟们不清白的得要啥样?”连一旁的树生都忍不住插嘴,不愧是桃花渡的半个秀才,读过书的人口齿伶俐,几句话就把锄头驳了个哑口无言。
“你们知道啥啊!你——”锄头见越描愈黑,更是委屈至极,不由火气直冒。
“锄头哥,别急,你有啥委屈当着大伙的面儿说出来,虽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是有的事儿以讹传讹,大家伙儿又道听途说,委屈了你事儿小,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你可担待不起,你说说,你们那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小午见锄头急的分寸大乱,跟自家兄弟争的面红耳赤,不由的出言劝慰。
“那晚上,我,我……”锄头急的满头是汗,支支吾吾了半天,却是自暴自弃的一声长叹,憋屈道:“我,我不能说!”
随后,便是无论田小午怎么劝解,众乡亲怎么义愤填膺的指责,锄头就是牙关紧咬,来来回回的只重复一句话,“小午,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我真的不能说!”
这么拉锯战的干耗了半夜,大家伙儿被锄头的倔脾气弄得食不知味,草草填饱了肚子各自回去了,那准备了一半的婚事在锄头极力反对中无限制的搁置,大伙儿都有些悻悻焉,原先好心贺喜的心态荡然无存,虽对锄头的话半信半疑,可因为锄头自己讲的不清不楚含含糊糊,大伙儿心中多半对锄头这种吃不认账又诸多狡辩的态度还是颇有微词。
街坊四邻散去,田小午便知道这十里八村今夜过后又多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话题,锄头今日这般越描越黑的行径,此事过了今夜就是想再解释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心中很为他今天的所作所为气恼,赌气的关了房门,想想自己一天的患得患失,还有仍然摆在面前的王家的这门骑虎难下的亲事,眼角酸的难受,可是看着锄头那皱眉纠结委屈隐忍的摸样,却心软的连借题发挥骂他一顿,自己发泄一番的狠心都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