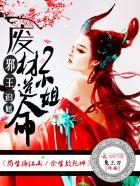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灰色地带的人是什么人 > 谈美文语言及其他(第2页)
谈美文语言及其他(第2页)
曾经就有人批评过余杰,说他文风威猛,有着强大杀伤力,在批评余秋雨、钱穆等人的文章里,就露出“文革体”的不良影响。也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左翼”作家文体甚嚣尘上、最终独行天下半个多世纪的传统之影响。
这个判断十分准确,也堪令人忧。
而余杰这么聪明的人都被绕了进去,大多数中国作家至今仍陷身泥潭,不能出拔,不能觉悟,贾平凹却是早在1983年前后就绕了出来,接上了沈从文那一代以数人之力,为“艺术而艺术”,抵制“左翼”文潮过于近视的功利化主张有害影响的“美文”传统创美文》杂志宏扬这个传统,的确难能可贵!
当年亲患,学汉语语言开始并没有语法,语法是后来引入的,为强调其科学性、可学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许多句子,用现代汉语语法裁断,就不很达标。
试举数个例子以说明。
汉语中的一大修辞方法是“通感”,打通五官,可视、可感、可触、可嗅、可品的都能互用。如“寺多红叶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风随柳转声皆绿,麦受尘欺色易黄”、“红杏枝头春意闹”以及小媳妇举着“闹轰轰一大把子通草花儿”等,在语法上都讲不通,与生活现实也大相违背:红叶怎么能烧人?风声如何可以绿?杏子、草儿怎样会争吵?这就是“通感”了的效果,其想象之新颖别致,实在是绝妙!到了现代的朦胧诗,里面的修辞日见了丰富与重叠。
美丽的中文系是一汪大水,我是水草里的一尾,厌光小鱼,许多目光锐利的鱼鹰正耐心地等待我们长大,并蓄意刁走我们的灵魂。
这诗说明鱼鹰似的教授,对学生像待小鱼那样,随时准备扼杀他们的生命灵性。透出学生的无奈,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上的失败等情绪。
可是,如果不以诗的语言来说,代之以直白的话,恐怕就没有什么味道,不值得看了。
假如说上面还只是一种修辞的话,那么到了“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引出古龙等人电影蒙太奇画面式的用语“古道,快马,一人绝尘而去”等章,数个,名词并列成句,叠出一组意象,语法上是怎么样都说不通的,却不害其意,而特别的形象逼真、简捷精练。
我说自己喜欢贾平凹的语言,其道理都包含在上面几例中,以见得平凹的不孤。
在我看来,贾平凹的语言是经得起细细把玩的,也耐看耐读耐琢磨,出味。这在小说里,可能还不太显明,被曲折的故事情节埋了;看他的散文或散文化的小说,以语言有味见长,就容易明白了。
比如谈文化的《老西安》、《秦腔》、《五十大话》,谈家世人物的《我是农民》、《祭父》、《我不是个好儿子》,谈景色世风的《白浪街》、《商州初录》等。他在《浮躁》诸小说里的景色描写,也可见出那种大散文家的风范来。
一流的作家都靠一流的语言来支撑,语言不好,故事再感人,也成不了一流作家,文章难得会传世。
像莫言,即使我和他师出同门,同在北京,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认识远在西安的贾平凹还早,但提起他的语言来,我实在喜欢不起来,认为它们太膨胀、夸张,爱走极端,没有节制,也很不凝练,直到《檀香刑》、《四十一炮》都还这样,那是很要命的事。
贾平凹的语言中,却绝对没有这些个观感。
他说“我们尊重那些英雄豪杰,但英雄豪杰辈出的年代必定是老百姓生灵涂炭的岁月,世俗的生活更多地是波澜不起的流动着,以生活的自在规律流动着,这种流动沉闷而不感觉,你似乎进入了无敌之阵,可你很快却被俘虏了,只有那些喜剧性人物增加着生趣,使我们方一日一日活了下去,如暗飞的萤虫自照,如不宿中的禽鸟相呼”。
如果用大白话改造一下,那一定会啰嗦得多,也没有现在这么流畅、富有生机,耐咀嚼了:“我们尊重那些英雄豪杰,可是英雄豪杰众多的年代,老百姓一定没日子过。
世俗的生活,一般是平淡的,自己沉闷地向前,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置身在里面,你失去了方向,迷了路,不过很快你就被它包裹了,只有碰见些有趣味的人,言行叫你难忘的,才能增加我们生活里的乐趣,加强了我们活下去的信心。”
等而下之,倘改成“洋八股”,就成了:“一方面我们呼唤时代的英雄豪杰,另一方面英雄豪杰太多的话,人民一定民不聊生,那是我们坚决不能答应的。虽然我们过不了平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是不能由你左右的,历史发展本身更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这样硬邦邦的语言,使人倒胃,却又是我们不得不每天在面对的。
如此,贾平凹的语言,就具有了一定的解构性.使我们身心放松,被一大股柔性的黏液包裹,自觉温暖自在。
贾平凹的文字中,还有特别阳刚的一面,并不就像李建军说的,只有“小女子气”似的呢喃。
我特别喜爱的一篇散文,就是他的《秦腔》,有贾谊、东坡之奔放的、一泻千里的气势: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京,豫,晋,越,黄梅,二簧,四川高腔,几十种品类;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日:秦腔也。正如长处和短处一样突出便见其风格,对待秦腔,爱者便爱得要死,恶者便恶得要命。外地人——尤其是自夸长江流域的纤秀之士——最害怕秦腔的震撼;评论者说得婉转的是:唱得有劲,说得直率的是:大喊大叫……别的剧种可以各省走动,惟秦腔则如秦人一样,死不离窝……这秦腔原来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一人籁的共鸣啊!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秦腔与他们,要和“西风”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馒一样成为生命的五大要素。
这样的语言,是何等风华气派!
沈从文曾在《湘行集·泊缆子弯》里说:“我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
贾平凹如沈从文,是写景的圣手,其小说“写景处,使人如同目遇”。小说要写景呢?
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一部。
看完了散文,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小说,看看起祥是如何起首的:
从榆林北的横山来到了延安,韩起祥就一直在延河桥头说书。那时的延河桥虽然还是一座木桥,冬天里铺架着,夏季长长的日子里却抽了木板放在小学校的土墩上当课桌,但那儿有一片空场子,有一个河神庙,来往的人多,三六九又逢着集会。
那个早晨,太阳还暖和,韩起祥就坐在庙门口,他穿得臃臃肿肿,小腿上系着竹板儿,睁着一双瞎眼,拨怀里的三弦。手的拨动和腿的闪动配合着,丝竹一齐价响,嘴里却含糊不清地发着肉声……
这是典型的贾平凹小说的叙事语言,景与人浑然一体,交代背景的同时,人物的身份、地位大体也就明朗了。即使它里面没有太多深刻的内容思想,甚至依然有一点领袖崇拜情结,但凭着这一点点高超、圆熟、生动的叙事语言,小说就很抓人,让人爱看。
如果没有长时期的文言阅读为底,善加描摹,又如何做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