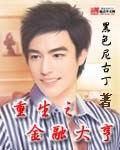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只想当备胎也不容易(快穿)90章免费 > 第85章 我当皇帝的那些年25(第1页)
第85章 我当皇帝的那些年25(第1页)
祁宴坐在床上,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下意识将头转向那边,正好和推门而入的祁闻淮四目相对。
说起来,祁闻淮比他还大上三岁,如今已经过了三十,但他的容貌上没有留下任何岁月带来的瑕疵,依然霞姿月韵、光风霁月。他应当是换上了常服来着地宫中,一身银白衣袍若霜雪,乌发半束垂落至腰间,雪衣乌发,清冷若仙。若说年岁和经历给他带来了什么,恐怕是他周遭越发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深不可测的气场。
从前的祁闻淮,虽然也不苟言笑,但是祁宴是能感知到他的情绪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皇兄挺好懂的。他虽然看起来清冷疏离,但其实很容易对祁宴心软,也很容易被他所取悦。
可现在站在祁宴面前的祁闻淮,他却有些看不透了。
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皇兄真正坐上了帝位,才有这般变化。
“皇兄。”看着祁闻淮一步步走来,祁宴不住轻声喊道。
祁闻淮的脚步在空旷寂静的地宫中显得格外清晰,似乎每一步都踏在祁宴的心上。
他最后在祁宴面前站定,他一双看不出情绪的凤眸微垂,静静地看着在床上,双手被镣铐所梏,浑身满是痕迹的祁宴。
祁宴觉得那神色是居高临下的,甚至带着一种厌恶和审判。
祁宴下意识将被褥往自己身上拢了些。自从醒来后,他成了那群人的阶下囚,更成为了他们随手把玩、供他们淫|乐的器皿一般的存在。这本就让祁宴深感受辱,如今在光风霁月的祁闻淮面前,似乎他还生出了一种自卑和胆怯。
看着祁宴将被褥往身上拢,祁闻淮的眸中似乎泛起了嘲讽般的笑意:“祁宴,你知道你现在看起来多脏吗?”
祁宴身上骤然发冷。檀钰冷嘲热讽他一万句,他最多只会觉得自己被曾经一个他没有放在眼里的小玩意儿嘲讽而感到屈辱,但是祁闻淮说他一句“脏”,他似乎就无法接受了。
“皇兄……”他下意识喃喃道。
“你不过是个野种,冠你‘祁’姓已实属皇恩浩荡,你也配称孤为皇兄?”与讽刺尖锐的话语不同的是,祁闻淮长眸中似乎透着怜悯。
祁宴十指轻颤,他觉得祁闻淮好像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明明之前,就算他被自己囚在深宫之中,就算他原本非常生气,但是也已经消气了不少。为何他把皇位“还”给他,他反而变得更加厌恶他了呢?
“皇兄……你怎么了?”他忍不住问。
“七弟和十弟,都是被你设计而死,是也不是?”祁闻淮突然问道。
七皇子和十皇子,原本是拥护祁闻淮这一方的势力。他们母妃之间关系亲密,几人也是从小就比其他兄弟关系要好。虽然天家复杂,就算是兄弟间,斗得你死我活的也比比皆是,但是他们之间也总有几个会有些许手足之情。祁闻淮和这两位皇子,便是如此。
他们是死于祁宴的设计,但是彼时四皇子正和祁闻淮处处针锋相对,于是最后这些都被祁宴嫁祸到了四皇子身上。他也怕祁闻淮责怪,因此一直隐瞒。
祁宴没想到这时候祁闻淮突然提到了这个,而且还发现了真相。不过事已至此,祁宴便也没什么好抵赖的,他点点头,说:“是。”
祁闻淮的神色随着祁宴的回答冰冷了一分,紧接着他又忽然问道:“父皇不是病危而死,而是被你下毒后再活活逼死的,是也不是?”
“是。”祁宴再次点头。
先帝在祁宴看来是他此生最仇恨最厌恶的人,但是他在祁闻淮面前,却确确实实是一个好父亲,弑父的名头本就不光彩,祁宴对外只是说先帝病逝,自然也瞒着祁闻淮。
祁闻淮神色愈加冰冷,他问出最后一个问题:“我母妃,也是被你害死的,是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