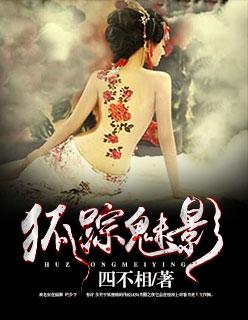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影视之旅从知否开始最新章节目录 > 第311章 大朝会(第3页)
第311章 大朝会(第3页)
后来还是皇帝看不下去,打断了众人的辩论,
“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此事就交给廷尉,纪爱卿啊,此事就交给你们廷尉查查好了,务必要差个水落石出!”
刚说完,纪大人刚要起身答应,凌不疑就插嘴道:
“陛下,臣有话说!”看皇帝同意,接着说道:
“自当日王隆出事后,臣便开始调查王隆父子,后来又经过对王隆的审讯,和排查他的来往信件,
终于确定这些信件军令都是文修君伪造的,
这一切都因文修君急需钱财,贴补给远在寿春的小乾安王,才令王隆铤而走险!”
接着拿出了不少伪造的书信军令,让皇帝查看。
皇帝本来就看文修君不顺眼,这老娘们仗着过往对皇后的恩情,一贯嚣张跋扈,再加上皇帝确实承接了不少老乾安王的遗产,怕烙下一个不好的名声,这才处处忍让,如今逮着机会还不修理她?于是怒道:
“岂有此理,这个文修君之前撺掇这小乾安王铸币,朕念在过去老乾安王的份上,只是罚她禁足,没想到,她可倒好,弄出如此多的是非,
也罢,既然她自己找死,那朕就也遂了她,
传旨,自即日起,收押文修君,革去她的封号,赐白绫!”
要说凌不疑这人心还是蛮硬的,只是死一个文修君还不罢休,立马说道:
“陛下,文修君不过是内宅妇人,不懂军情利害,
但王淳放任妻儿糊涂行事,不当再局朝中!”
要知道凌不疑可是一贯‘支持’太子的,属于太子党,他这么穷追猛打,越侯等人自然大喜,纷纷落井下石,弹劾王淳,
一时之间朝廷之上都是讨伐王淳父子的声浪,就是那些本来支持太子的人见凌不疑首先发声,也不知道该如何行事,一时间都没了方寸,
只有寥寥几个和王淳交好的帮忙出声,也淹没在讨伐的风浪之中
太子亲自下场帮助王淳辩白,不过他本性纯良,不善言辞,诉说的理由难免仓软无力。
景昊郢是坐在旁边和五皇子一起看热闹,他也是不打算再帮王淳说话的,当日他都提醒过王淳,可是这王淳连文修君都没搞定,事情的收尾也没整利落,还被凌不疑抓住了把柄,这也怪不得旁人,
只是看太子势单力孤,多少有点儿可怜,
本来事情也就这么地了,文帝也准备宣布对王淳父子的处罚,
偏偏有些人眼见太子失势,想要上前踩一脚,首先发言的就是御史中丞左大人,这老小子最不是东西,直接就是张口道:
“陛下,外戚嚣张跋扈,不是一天两天了,依下官来看,定是有人监管不力所致!”
说着还看了一眼太子,这下大家都知道这小子所指的是谁。
越侯本来也想踩上一脚,后来一想他其实是越妃的兄长也算外戚,这才没有开口,不过他不开口,下面的可以说话,不少人纷纷开始指责起来,虽然明里没有点名,其实都是暗指太子。
一时之间,太子又陷入了众矢之的,
太子无奈之下看了看曾经的太傅楼经,只是这老小子老神在在差不多跟闭目养神一般,连个眼儿都不跟太子对视一下,更别提开口帮忙了,
太子又看向凌不疑,凌不疑只是面无表情的不说话。
突然,有人说道:
“诸位大人所言,下官以为不妥!外戚行事,不应是某一人监管不利所致,而是要看外戚本人,如果真要找这个人的话,那也应当是陛下,因为陛下的关系,外戚才有地位,莫不是众位大人在责怪陛下?”
这有别于众人的言论一出,大家都纷纷望去,太子是欣喜,毕竟这是帮他说话的,
景昊郢也是一脸好奇的看了过去,竟然是许久不见的楼犇,这小子也在朝堂之上,不过地位较低,坐的很是偏僻,景昊郢之前竟然没有注意到他。
不过,楼犇这话一说,马上坐在他旁边的袁善见就反驳道:
“楼大人此言差已,陛下日理万机,怎会有精力来监管外戚,
再说了,外戚是后族亲眷,理应有皇后,皇妃监督才是!”
接着两人引经据典,说了一大堆,这两人本来就是同窗,现在又同在廷尉府,又博学多才,
楼犇认为外戚更多的应该是自省自查,不应怪罪他人,明显帮太子说话,
袁善见的意思是外戚乃是后宫亲眷,因为后宫的关系得享富贵,后宫必须起监督的作用,到是纯中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