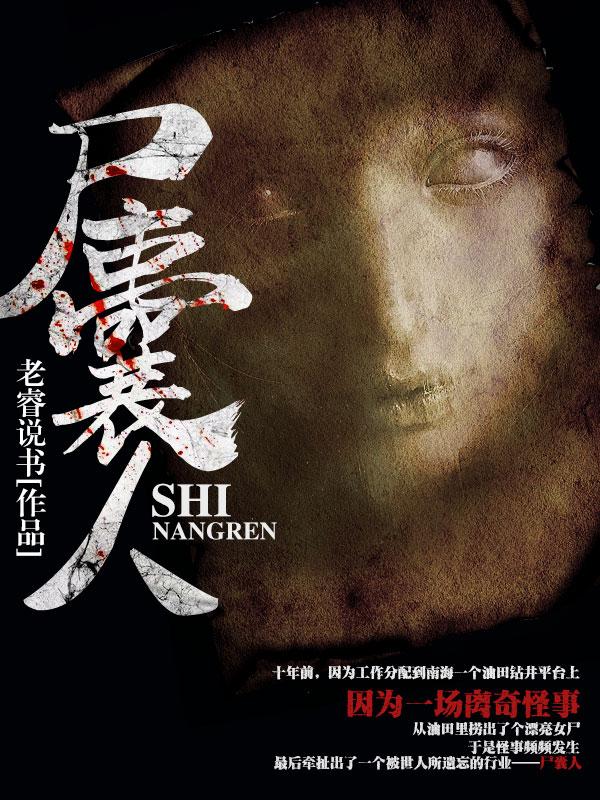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人类的饲养员送餐员 > 第317章 留不住(第1页)
第317章 留不住(第1页)
比起喻清收获了萤火虫后跌宕起伏的心绪,另一个获得这些星星的人,裹在毛毯里,睡得十分安稳。男孩已经睡得熟了。唐柔摸了摸他的额头,已经退烧,随后伸手去抽被他紧抱在怀里的瓶子。中途险些把他吵醒。男孩将瓶子抱得很紧,紧到像珍贵的宝藏,手指抓到泛出失血的白色,最后还是在唐柔的轻声安抚中,慢慢松了手。小月抿着唇,有些期待地感知着唐柔的动作,没想到她并没有把那一瓶萤火虫给他,而是打开车窗,拧开瓶盖,将那些被闷到奄奄一息的小虫放了出去。咕嘟一声。水舱冒出一串泡泡,少年沉到了水底,背对着唐柔蜷缩在一起。唐柔觉得好笑,蹲下去敲敲玻璃璧,“你又不能碰这些东西,干嘛还想要?”
水母不理她,脸颊埋在手臂间,抱着双膝一动不动。“更何况,你又看不见。”
月的手上有毒素,这些毒素在碰到唐柔时可以很好的控制,可这种自制力在碰到除她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那么不堪一击。道理都懂,可他不能接受自己的自主送给了别的生物那么浪漫的礼物,而到了他这里,什么都没有。唐柔围着毯子,找了个靠垫,在水舱旁坐下,温声哄不开心的水母。“那些小虫子闷久了会死的,它们的生命很短暂,寿命只有几天。”
在短暂而又璀璨的生命中,它们应该飞舞在广袤的自然里,点亮夜晚,而非小小的玻璃瓶中。它们只能璀璨很短很短的时间。唐柔感谢它们让失去亲人的男孩做了个好梦,也希望它们能够在短暂的生命中见天地。少年动了动,终于转回身,打开舱盖,慢慢从水里爬出来。唐柔觉得好笑,歪着头看他,“不生气了?”
月垂着眼睫,扯了一条毯子,细细地擦拭着身体上的水渍,等把身体擦干后,慢慢地依偎在她身旁。他怎么会生她的气。喜欢她都来不及。唐柔将身上的毛毯拉开,裹住他冰凉的肩膀,两个人脑袋挨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体温。其实月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人类世界的语言与他而言太过复杂,他能做的,只是感知唐柔的情绪。唐柔的情绪很好,很平静。对待他时总带着宠溺和纵容,这种甜美的感知让他忍不住多了一点小小的私心,不想让别人分割走她的注意力。萤火虫应该飞舞在夏天的夜晚,而非玻璃瓶里。他知道了。月抬手,托着唐柔因为困倦而一晃一晃,昏昏欲睡的脑袋,让她靠在自己肩膀上。有她在就好了,别的他都不要。然而他懂了,有人却不懂。距离残破装甲车几公里外的街道上,原本人声鼎沸的酒吧现在显得有些清冷。今晚那个应该站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主唱不在,他消失了,没有请假,也没有打招呼。酒吧的二楼,店长擦着额头上的冷汗,望向不远处站在落地窗旁身着神圣长袍的男人。对方身上正散发出极其不悦的气息,让他感到十分不安。“那他昨天去哪了?”
牧师身旁的信徒像他的代言人,皱着眉问老板。老板头皮发麻,哆哆嗦嗦地回答,“昨天不是被您的人带走了吗?”
男人皱眉,他身旁的信徒立即又问,“卡佩先生问的是他昨天从先生那里离开后,去哪儿了?”
酒吧老板脸色发白,急得发抖,“不知道呀,他昨天就没回来!”
“一整晚没回来?”
“没回来,那天晚上没回来,整整一个白天都没回来,现在又翘掉了今晚这场的演出,我们已经将近三十六个小时没有见到他了!”
时间逼近12点,牧师身旁的信徒上前提醒,他还要回到中心大教堂带领诸位信徒咏唱颂歌,赞美神灵。男人冷哼了一声,极度不悦。信徒们一字排开,在他身旁垂首恭敬地让出一条道,场面安静肃穆得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等这些身着长袍的人的身影都从走廊深处消失后,老板才颓然地坐在地上,后背的衬衣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冷汗打湿了。太恐怖了,被牧师盯上的感觉就仿佛被毒蛇盯上,让人恍惚间有种下一秒就会被咬断喉咙的错觉。由于自由日的存在,城市中有许许多多失去了主人居住的空置房屋,有些被流浪汉占领,有些则是成为都市男女偷情私会的隐秘场所。在距离酒吧街几公里外,有群高耸入云的百层高档单身公寓。被无数人苦苦寻找的喻清,正在其中一间窗户被砸破的房屋中,静静地坐着。他垂着头,清瘦的脊柱一节节凸起,长而柔软的兔耳从发丝间滑落下来,遮住了眼。许多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会以为这对兔耳是假的,是为了迎合酒吧观众而戴上的猎奇头套,像个增添趣味的逼真装饰品。可如果凑近了仔细看,会发现这些兔耳太过也太过精细逼真了。薄薄的皮层和柔软的白色短绒下,是一根又一根清晰的毛细血管,仿佛其中正在流淌着温热的血液,而如果有人此时将手覆在这双兔耳上轻轻抚摸,还会感受到它在掌心下跳动。只不过这一刻,它们看上去倒真像假的。喻清也像假的,僵硬的、不会动的傀儡。如果不是胸腔还在缓慢地起伏,会有种错觉,让人以为他已经在这座无人的房屋中安静地死去。房间凌乱得像被强盗洗劫过。他的脚旁满是摔碎的玻璃,几个酒瓶滚到了不远处,酒液洒了一地。桌子上有两个空了的药瓶,旁边还扔了一根燃了一半的香烟,他尝试了几次都抽不进去。苍白修长的手指紧紧攥着一个玻璃瓶,里面有数十只已经死去的深褐色的小虫子。所谓的星星,熄灭后,竟然如此丑陋。细碎的发丝下,喻清睁着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像是不会眨动一样木然地看着手中的玻璃瓶,眼球因为干涩而溢出自救性的生理泪水。他不觉得悲伤,只觉得痛苦。他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能力。他只是徒劳地抓着手里的瓶子,陷入了白日梦魇。这是噩梦,对吧。如果是噩梦,为什么还不醒?可如果它不是噩梦,为什么会那么糟糕?一切都很糟糕,他的生命,一团糟。为什么有人说天空是蓝色的,阳光是温暖的?花开了会有清香,下过雨之后会有彩虹,为什么别人说的这一切,他都没有见过?为什么他得到的东西总会总会离他而去,无论如何挽留都是徒劳。为什么它们会死去?明明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满心欢喜地抱着这个瓶子,甚至不舍得眨眼睛,从日出到日落,看着这些飞舞的萤火虫,好像心脏都被它们点亮。他甚至产生了名为幸福的错觉。直到那些光点渐渐地暗淡下去。起初,他尝试拯救它们,可无论他怎么做,那些小飞虫的生命力就像被未知的力量抽干一样,渐渐不再发光,到了最后,躺在瓶子里,安静而无声地死去。他留不住。如果没有看过星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