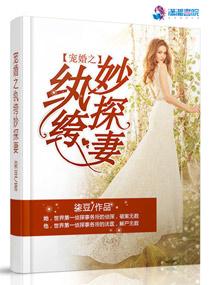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重生之爽约txt > 第38章 公主驾临(第2页)
第38章 公主驾临(第2页)
景阳公主看着面前神态慵懒的女人,那眉皱的更紧了。
他又纳别的女人了?府里原来的这些还不够吗?看她的样子倒是也有几分姿色,但是——她也配住在这个院子里吗?
当年,他和她在这院子里,可是恣意欢爱过的……
景阳公主的脸色十分难看,鼻端冷冷的哼了一声,也不理会爽儿,只自顾自的在屋子里信步走了起来。
行走时,不时摸摸屋中摆放的物件,似是回到自己房中一般随意。
一切都是之前的样子,连那张贵妃榻都还是摆在窗前,当日,他可是最喜欢和她在那榻上欢爱的;他十分迷恋她,便是后来她嫁了人,他也敢色胆包天的去找她,再后来她成了寡妇,他来的就更勤了。只是一年前,他生了那场病后,就突然不理她了,难道是因为她没有过来探望,他恼恨她了?
景阳想着那个薄情的男人,心里升起一种似怨似念的情绪,突然就觉得十分燥热,一抬眼,看到屋角,眼睛闪了下,“怎么放了这么多火盆?”
金氏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也愣了下,目光瞟向爽儿,瞬间带了丝了悟,唇角嘲讽的扯起,“公主,侯府里的规矩,主子的房里都是只放两个火盆的,这屋里放了四个,怕是因为有人身子弱、怕冷,侯爷怜惜些吧。”
“怜惜?”
景阳的眉立了起来,她的眼睫抬起,目光阴郁的望向窗前的女子,“谁又是三十六个月生出来的,怎么就比别人娇贵呢?”责怪的瞪了金氏一眼,“下人夺了主子的份例,你这家是怎么管的!”
金氏忙惶恐的垂下头,“公主教训的是,妾身无能,一心只想着服侍侯爷满意,却是御下无方,这院子……”
“这院子本就是主子住的,她不过是个下人,怎么配住在这儿!”
她是金枝玉叶,她用过的地方,别的女人怎么能住!
景阳厉声说,目光狠狠的盯着爽儿。
爽儿感受到来自那人的恨意,心里不由一沉,她知道景阳是先皇最宠的女儿,当今天子也让她三分,自己是万万得罪不起的,于是沉默的垂着头,做出十分恭敬的样子:对待这种泼妇最好的法子是装聋作哑,她闹腾一阵觉得没趣大约就会罢手了。
景阳见爽儿不言不语,心里的怒意反倒更甚了,正想再开口责难,门外突然响起男人的脚步声,她心里一喜,抬头看向门口:果然是逍遥侯进来了!
景阳已经有一年没有见到逍遥侯,今日见了,觉得他比印象里更英俊了,身上还多了一种说不出的气质——他那双眼睛亮得跟夜里的明灯似的,目光凛冽犀利,只看她一眼,就让她芳心乱颤,恨不得像飞蛾见了火,奋不顾身的扑上去。
景阳见了自己的情人,心花怒放,早把爽儿放在一边,一双妙目黏在樊离身上,幽幽的,“你来了。”
便像妻子见了丈夫归家一般。
樊离看了景阳一眼,也不应答,只微微点了点头,便直接迈步进来了。
似乎是随随便便的走过去,却恰巧停在景阳和爽儿之间,用身躯隔断了景阳望向爽儿的视线。
他看着那个美艳的贵妇,略扬起唇角,“公主今日怎么有雅兴造访本侯的陋宅了?”
樊离的印象里有这个女人,确切的说,是逍遥侯的记忆里记着和这个女人每一次欢爱的情景,他清楚她这次过来是为的什么,可是如今这身子的主人已然换了,他对她没有兴趣。
他那句不咸不淡的话听到景阳耳里,却是另一番滋味。
她想着从前他每次见到她,都是那么迫不及待,恨不得把她吃进肚里去,抵死缠绵时总也要不够,还没分开便又约了下次幽会的日期——怎么如今他竟这么淡然了?是他真的对她没了那份心思,还是,碍于别的人在场,不好表露呢?
景阳心里酸溜溜的,视线被逍遥侯挡着,看不到他身后的女人,便只能都落在男人身上,贪婪的扫视着他强健伟岸的身躯,“侯爷总不过去,本宫便只能过来了。”抬起眼来迎着樊离的视线,“本宫那里又没有老虎,侯爷怕什么呢?”
挑逗的意思太明显了。
连金氏面上都有些挂不住,爽儿偷眼看到金氏脸涨得通红,却又碍于景阳的权势不敢出声,只能低头隐忍,心里禁不住想笑:外面的情人找上门,家里的就只能受着了。只是,那情人是只母老虎,家里的这个是条狼,那禽兽艳福不浅,配这如狼似虎的两只,倒还真是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