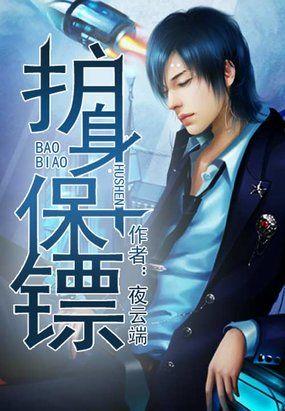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逆光的星星 > 第47章 采访1(第2页)
第47章 采访1(第2页)
但是,每一次,她看到的,却都是他灭烟时,眼底深处的那一点疏离。
他对她是那样彬彬有礼,跟绅士一般。
举手投足之间无可挑剔。
“对了,三哥,就是这样的,对客人就是这样就完美了。”
当年,当他完美地演绎出她教他的系列礼仪时,她就是这样说的。
如今,他又一次完整而至臻至美地在她面前演绎了这一套礼仪——对着,她这个最初的老师!
如同现在,他灭了烟,走到她面前,拉开她前方几步远的一张椅子,很绅士地做了个“请”的姿势。
然后不忘给她开上一瓶她最喜欢的**水放在椅子前面的桌子上。
“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吧。”
直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程亦鸣才慢慢开了口,“且不说那个专题本来就不是我们杂志的专攻,就算是,这事也已经过去了……”
“谁说过去了?”
夏文丹算是个执着的人,一旦她认定的事,几头牛也拉不回。
如同现在,对死去农民工的怜惜让她已经自动忽略掉程亦鸣的疏离。
她一屁股坐在他为她拉开的椅子上,拿起那瓶开了的**水喝了一大口,“你知不知道,三哥,我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那个农民工会张着血淋淋的手对我摇晃,让我为他伸冤!”
程亦鸣的眉头略蹙了下,“你二哥同意了?”
“反正他没反对。”
她望着他,这样的程亦鸣让她有些陌生。
小时候,他是最好打抱不平的那一个。
想当年,他也是替她打了那个抱不平,才成了她的“三哥”;那些一起成长的岁月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几乎已经成了他的代名词。
但是,现在,他蹙着眉,指尖在桌面上并无节奏地敲击着,仿佛她跟他说的这件事是件实在让他为难的事。
可是,她不管。
从小,她夏文丹决定的事,便一定要办成!从无例外,从无失败!
“三哥,”她望着他说,“我二哥还说,为了方便,让你跟我一起去完成这个专题。”
他的眉蹙得更凶,深深的“川”字让他一下子似乎老了10岁。
“你不许拒绝!”
她看到他张了嘴,抢在他说话以前说。
不论他想说什么,这一刻,她都不想听。
“我没有想过拒绝。”
他抓起一支烟,想了想,又放下,“我只是想说,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个题,让我来牵头,你配合,可好?”
她蓦地有些发懵,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她笑:“你开什么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