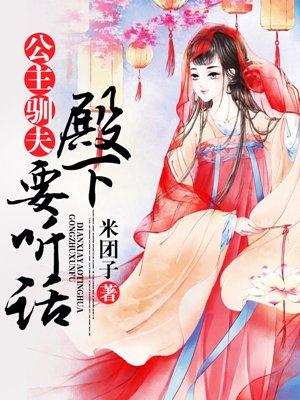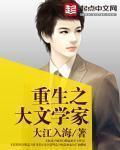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重生之财色巅峰全文免费阅读 > 第五节 虚张声势(第2页)
第五节 虚张声势(第2页)
一连几天没等到赵一民的答复,她有点坐不住了。
刘素芬从来不是个有主见的人。
一番患得患失的思想斗争后,她瞒着杨昆找到了那位本家亲戚。
得到的答复是:原来的1万元报价不变,没有额外的附加条件。
卖就卖,不卖拉倒。
刘素芬心事重重地回到家,坐在椅子上生闷气。
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就直接卖了,也免得落下贪心不足的名声。
她的表情没有瞒过善于察颜观色的杨昆。
再三催问之下,刘素芬道出了实情。
杨昆顿足捶胸,“妈,你去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在他看来,买卖双方的底牌都已经亮出来了,现在正是拼耐性的阶段。
谁耐不住性子,就是主动服软,就得做出让步。
刘素芬也有些追悔莫及,她问儿子:“现在怎么办?”
杨昆一咬牙,“咱们自己盖!”
刘素芬一愣,“不卖了?”
“卖,但不能主动求人家买,咱们摆个姿态,吊吊他们的胃口。”
刘素芬担心地看着他,“要是人家真不要了怎么办?”
“那就把房子盖起来,钱不够,我卖血去!”
消息通过中间人传到赵一民的耳朵里,他呵呵一笑,“虚张声势罢了,孤儿寡母,家徒四壁,负债累累,盖房,笑话!”
中间隔了一天,杨昆跑到砖厂门口,拦了辆送砖的拖拉机。
一车4000枚粘土砖不过百十来块钱,就算自己不用,转手也能卖掉,拿来虚张声势最合适不过。
下午,赵一民乘车去县工业局开会,特意从环城路口绕了个圈。
他看到了码得整整齐齐的两垛红砖。
当天夜里,一垛砖墙不知被谁推倒,红砖散落一地,摔碎得也有不少。
刘素芬心疼得不行。
杨昆皱了皱眉头,他不能确定这事是赵一民使坏还是哪个顽皮孩子干的。
于是他搬起家里那张旧钢丝床,带了蚊帐和水壶,自己住到了工地上。
一连两天,风平浪静。
第三天,杨昆又往工地上卸了2吨水泥。
刘全保安排了俩小工,用了一天时间,把施工现场和备料场地清理了出来。
赵一民心里犯嘀咕,但还是沉住了气,决定静观其变。
这时,麦收开始了。
杨昆家按人头分有1亩1分自留地,二叔家里地更多。
即便有二叔帮忙,他和母亲也用了2天才把麦子收完,借了辆农用三马车拉回了家。
收完小麦,接着种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