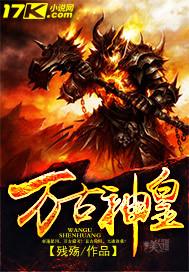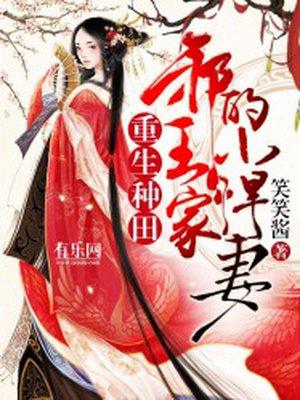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什么意思 > 第5章 被羞辱后更加勤奋(第2页)
第5章 被羞辱后更加勤奋(第2页)
仲尼虽然在少年时期曾帮着母亲干过许多杂活,然而,对这个一贯以贵族子弟自居的青年人来说,毕竟不能把种田、放牧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
母亲的离世,让仲尼的生活更加艰难了。他整天除了学习就是谋划自力更生的办法。于是迫于生计,他选择了襄礼助丧的职业,当时称作丧祝,就是专门为贵族和富裕的平民主持、操办丧事。
按照中国古代礼制,当时的丧礼活动十分复杂,也颇为讲究,尤其是富庶人家的丧礼更是隆重奢华。
这种襄礼的活动在西周时期大概是由王室和诸侯国的神职人员巫、祝之类主持的。后来,随社会发展,神职人员地位开始逐渐下滑,他们逐步散落民间,便成为专门从事丧祝。
后来,襄礼不再是贵族的特权,一部分富裕的百姓在丧葬礼仪上也开始讲究,因此丧祝需求增多。如此一来,丧祝开始成为一部分民间知识分子的正式职业。
当丧祝的人,需要身着特制的礼服,头戴特制的礼帽,当时称之为“襦服”。“襦”与“儒”同音,人们便逐渐直接称丧祝为儒。因为孔子长期从事这种职业,他创立的学派也就称为儒家学派了。
孔子对丧礼的掌握同样经历了由少到多、由不熟练到熟练的过程。他关于丧礼的许多学识,也是来自于做丧祝的过程之中。
在那尊祖宗、敬鬼神的古代,人们对待死去的先人要比对待活着的人重视得多。丧葬祭祀活动也日益隆重而繁杂。贵族发丧时,场面浩大,涉及人员众多,丧礼繁杂而又考究。
据古籍记载,从人死到下葬前的礼仪程序就有抹浴、饭含、小殓、小殓莫、大殓、殡、奠、朝夕苦、荐新、启殡、载柩、朝祖、行柩等五十余项。每项都有复杂的规定。各个程序和环节所需不容的丧具以及它们如何放置,也都有约定俗成的要求。
襄礼的儒要负责指导和安排数以百计的参加丧事的各类亲友。同时,儒者本身设物执事、一举一动都有严格细密的规定,儒者必须一丝不苟地加以履行。
从事这种复杂而严谨的襄礼业务,需要对丧礼各方面知识熟练掌握。这门职业其实是很辛苦的,既要操心,又要劳力,还要小心翼翼地保证参加葬礼的人不出现疏忽或差误。
可是孔子却尽心尽力地去从事这一职业,而且是一直做到晚年。
孔子在晚年回忆自己曾经的生活时,说:
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所谓“丧事不敢不勉”就是对他在襄礼过程中认真,尽职的真实写照。在从事襄礼职业过程中,孔子的知识、经验越来越多,对业务也是越来越熟练。
孔子虽然严格认真地从事助丧襄礼,但是却不满足于做传统的儒者,不满足于能熟练地重复世代沿袭的基本相同的程式,不满足于礼乐知识的简单掌握,不满足于这不体面的“鄙事”和仅仅把礼乐知识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
从墨家攻击孔子以后的那些为求食而做儒者的情形,似乎可以窥见早年此类儒者视为君子所鄙视的。
孔子向往和追求的是个人生命价值可得以展现的职业;是发现礼的意义,追究礼的大体,探索蕴含在礼乐中的社会、人生哲理;发现礼的规定中所蕴含的精神、“所以迹”、道义等。
因此后来,孔子便逐渐由丧襄礼之儒向新型的学者之儒或曰道义之儒发展变化,最终成了名副其实的“君子儒”,成为我国历史上由传统“襄礼之儒”向“儒学之儒”转化的第一人。
孔子在从事丧祝工作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刻苦学习,所学知识很快就超出了当时贵族学校规定的礼、乐、射、御、书、数六大科目,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
因为孔子很有学问,他主持和策划的丧祝与一般人主持的丧祝完全不同。
他在为人家进行襄礼活动时也干得特别出色,并且时常有些新颖的活动加入传统的襄礼中,使原来显得死气沉沉的活动变得有声有色。因此,许多显赫的贵族家庭在有需要时都特意前来请他。
孔子因而名声越来越大,就连鲁国国君也开始注意他了。看小说,630book。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