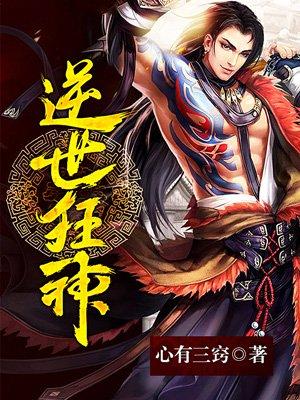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斗兽棋怎么玩才能赢 > 第十九章 各有盘算(第1页)
第十九章 各有盘算(第1页)
掌灯时分,珠市口燕来楼的雅间里,早早的就掌上了几盏满堂红的大油灯。再加上雅间里安着的四盏莲花电灯放射的光芒,更是把个不算太大的雅间照得纤毫毕现。
八仙桌上,四冷盘四热荤已经摆上了,压桌子的大菜是一条黄河大鲤鱼,刚从河里打上来就趁着鲜活扔进猪油里,再搁冰块箱子里快马送到的四九城。到厨下把冻得硬邦邦的猪油化开了,那黄河大鲤鱼居然还能动弹几下,赶紧着做成一道鲤鱼焙龙须面,皇上的御宴上也是一道能抢了头彩的好菜!
几个景德镇白瓷做的酒插子里,滚热的水把山西老汾酒温得香气四溢,混着从桌子上散发出来的菜肴芳香,着实叫人馋涎欲滴!
看着燕来楼里专门伺候雅间的跑堂把最后一道西湖莼菜羹轻轻放到了桌上,端坐在主座上的齐三爷轻轻一摆手,侯在齐三爷身后的管家立刻抬手把一块大洋扔到了那跑堂的怀里,朝着雅间门口努了努嘴。
看也不看那默不作声鞠躬谢赏后退出了雅间的跑堂,齐三爷伸手从自己身后伺候着的管家手中接过了一张纸条,递给了坐在自己身边一名很有些干瘦的中年人:“这是今儿一整天半月楼后院赌局进项的明细,照着往年的老规矩,各位都看一眼吧!”
也不接齐三爷送到了自己眼前的纸条,那很有些干瘦的中年人晒笑一声,自顾自地端起了自己面前的小酒盅:“就这么仨瓜俩枣的散押账目,往年里也没人乐意看!大家伙捧着三老爷您攒了这个局,估摸着也都信得过三老爷!这个。。。。。。就不必了吧!”
频频点着头,另一个同样端起了小酒盅、身穿着一套烫金描边马褂、留着一条花白长辫子的老人也哑着嗓子应和道:“都是四九城里场面上走着的人,谁也不会盯着那几个小账!老头子冒昧,问齐三爷一句——今年几个大户押进去的账,齐三爷能交个实底么?”
抬眼看了看坐在另一张椅子上默不作声、只顾着自己闷头大吃的胖大汉子,齐三爷不动声色地将那张纸条放在了桌子上:“那段爷的意思呢?”
吃得满嘴流油,那胖大汉子翻手指了指挂在雅间角落衣架上的一件巡警服,含混不清地笑道:“齐三爷这话可就说得矫情了!我姓段的不过就是珠市口一个臭巡街的,在这场面上,我姓段的放个屁都不响!有啥话,齐三爷你们唠明白了,我姓段的跟着走就是!甭问我,甭问我!”
端起了自己面前的小酒盅,齐三爷轻轻啜了一口温得恰到好处的山西老汾酒,慢条斯理地点了点头:“既然几位都让我交个实底,那我也不瞒着诸位了——今年攒的这局,只怕要崩了底子!”
毫不吃惊地用手中握着的小酒盅轻轻叩着桌面,那干瘦的中年人面无表情地说道:“攒局求利,原本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买卖,讲究的就是个愿赌服输!按着以往订下的规矩,无论输赢庄家都占了七成,剩下的三成算是剩下的三家帮庄!既然齐三爷都说今年的赌局要崩了底子。。。。。。那齐三爷给个痛快话,抛去了德胜门齐家该赔出去的七成,剩下那三成,我们一家要赔多少?”
轻轻将手中的小酒盅放回了桌子上,那留着一条花白辫子的老人也是频频点头:“秋虫会上攒局,咱们这四家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也罢。。。。。。齐三爷给个数目,我这就回家备银子!”
冷冷地盯着那留着花白辫子的老人,再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身边那干瘦的中年人,齐三爷冷笑着哼道:“四九城里打行的舵把子、民国政府里的清客首领,再加上珠市口儿的段爷。。。。。。噢,我这儿还给弄忘了——听说段爷马上就要高升了?就您三位的身家,别说赔出来今年秋虫会这赌局的一成,那就是全都让你们掏了,也不过就是三位翻翻手的事儿?!”
也不等八仙桌上坐着的其他三人开口说话,齐三爷已经伸手从自己的袖子里摸出了另一张纸条,轻轻放到了桌子上:“今年秋虫会上的斗蝎邪门,除了井水胡同的纳九伺候出来一只七杀蝎,还有个没摸明白来路的公子哥儿,也鼓捣出来一只用点金石伺候出来的野蝎子!单就是这两门,前前后后就得有十来个大户朝里面砸钱!我这儿请教三位一句——一万、一万三、两万,这三个数儿,三位听着耳熟么?”
伸手一抹油腻腻的嘴唇,段爷很是四海地大笑着端起了自己面前的小酒盅:“既然是攒局,那不就是有庄有闲、将本求利么?!敞开大门收银子,宝盅一开论输赢,进出凭运气,输赢靠老天!我也不瞒着齐三爷,那押在纳九身上的一万三,是兄弟我的!”
同样光棍地点了点头,那干瘦的中年人脸上飞快地闪过了一丝阴冷的颜色:“打行里的兄弟们命苦,刀头子上舔血混口饭吃,今日不知明日事。有眼皮子浅薄的兄弟想赚几个快钱收山养老,齐三爷您也得包涵着些!”
干咳一声,那留着花白辫子的老人也是慢条斯理地点头称是:“清客者,清苦之过客也!说句该打嘴的话,哪天这民国也像是大清朝似的倒了城头大王旗,兵荒马乱之中,我等清客,也就只能依赖着在这秋虫会赌局上得来的几个小钱,求个三餐温饱、一榻容身了。。。。。。”
仰天打了个哈哈,齐三爷眯起了眼睛,来回扫视着雅间里几个共同攒局的同伴:“几位的话,倒也的确是有几分道理!攒局开赌,几位真金白银的押上来,要是赢了,那庄家就得真金白银的赔出去。。。。。。”
不等齐三爷说完,段爷狠狠地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震得八仙桌上杯盘乱跳:“痛快!到底是德胜门齐家主事的爷们,吐口唾沫砸地上就是个坑!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一码归一码,坐庄该赔出去的那一成,我一个大子儿都不赖;要是我押对了宝,那齐三爷肯定也是。。。。。。”
同样打断了段爷的话头,齐三爷也是狠狠一拍桌子:“自然是立马照赔!”
眼中精光一闪,那干瘦的中年汉子与那留着花白辫子的老者几乎同时端起了自己面前的小酒盅,遥遥朝着端坐在椅子上的齐三爷一举:“齐三爷爽快!”
同样端起了自己面前的小酒盅,齐三爷却只是浅浅地啜了一口,却又再次将那小酒盅放回了桌子上:“既然几位都说我爽快,那我今儿也给诸位交个实底——花旗银行里面,兄弟我存了五十万大洋!德胜门齐家名下的产业,分到我手里头的,一天之内也能变现个四五十万!既然诸位都这么看好了纳九,那兄弟我也不矫情——这差不离一百万大洋,明儿我就全押到纳九身上去!”
得意地看着八仙桌边那几张骤然间变得瞠目结舌的面孔,齐三爷回头看了看侍候在自己身后的管家:“别光傻站着,给几位爷算算,这么一倒腾下来,德胜门齐家得赔出去多少?这几位爷该掏的那一成又是多少?”
从袖子里摸出了个小巧的算盘,管家一边飞快地拨弄着只有樱桃核儿大小的算盘珠,一边念念有词地絮叨着:“照着眼前的赔数算,德胜门齐家倾家荡产,勉强算是能赔出来眼下收了的所有押票!这三位爷。。。。。。差不离一人掏个小二十万大洋,也就齐活儿了!”
将自己面前小酒盅里所剩无几的山西老汾酒一饮而尽,齐三爷很是得意地举着手中的空杯,笑眯眯地看向了同桌的三人:“几位爷,虽说过了今年的秋虫会,德胜门齐家就算是在四九城里没了字号,可我齐老三还在,还能吃香的、喝辣的,斗蝎攒局玩戏子!到时候要是还有什么好局要攒,几位可千万别忘了我齐老三!”
‘哗啦’一声,那干瘦的中年汉子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一双生得颇为狭长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齐三爷那带着笑容的脸孔:“齐三爷还真是。。。。。。好手段!以势压人,您倒真是不怕嘴张得太大了吃噎着?!”
伸出了一双巴掌,那留着花白辫子的老人也忙不迭地站起了身子,只顾着将伸出的两只巴掌胡乱摇晃:“这可使不得啊。。。。。。齐三爷,老朽这两万本金。。。。。。得之不易,这可是老朽的棺材本啊!若是。。。。。。二十万,真要是让老朽赔出二十万大洋,只怕齐三爷就只能在永定河中看到老朽这副枯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