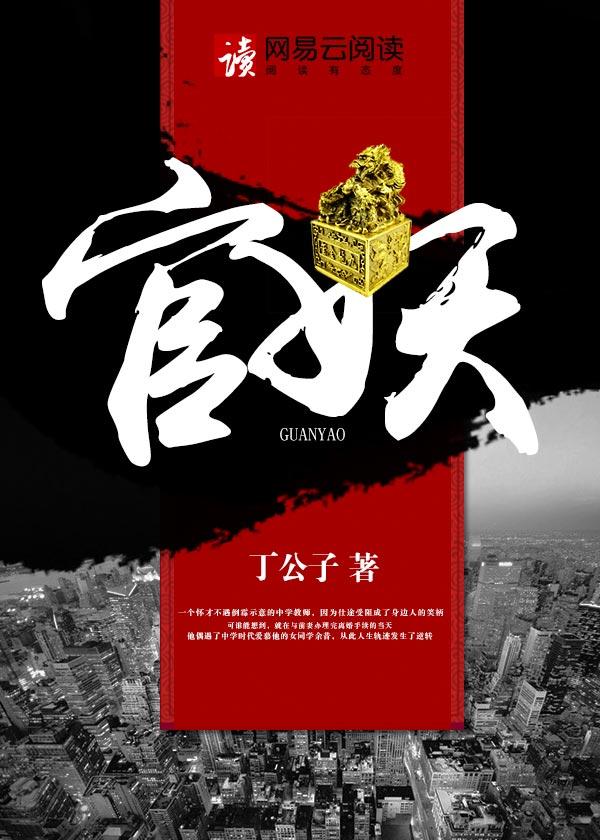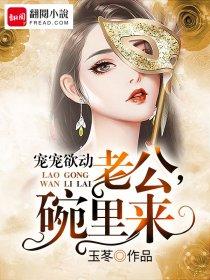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金军围城重生宋钦宗女主 > 第1223章 父子的谈话第一更(第2页)
第1223章 父子的谈话第一更(第2页)
“爹爹,孩儿最近有一件事不太明白。”
“什么事呢?”
“孩儿听说最近许多人都在讨论东征日本国的事情,有人说不要东征,说是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宋日贸易,有人又说要东征,番邦不好好教训,日后必成大患。”
赵宁看了一眼赵瑾,赵瑾问的很认真。
赵瑾继续说道:“有人跟孩儿说,要多听多方的说法,所谓兼听则明,但孩儿在听到这件事上,却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对这件事无法阐述自己任何想法。”
赵宁摸了摸这小家伙的脑袋,笑道:“你没有自己任何想法,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为何你在九岁的时候,就非要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了呢?”
“可是我去问过那些老师,他们说父亲九岁都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了。”
“他们骗你的。”
“骗我的?”
“你父亲我是大宋的官家,他们提到官家,自然要说官家小时候就是人中龙凤了,不然他们若说官家小时候不读书,整天只知道玩,这传到我的耳朵里,他们担心自己丢饭碗。”
“那他们都很怕父亲。”
“你不怕吗?”
“我不怕啊,我为什么要怕我的父亲呢?”
赵宁叹了口气,说道:“你还小,读的书,走的路,都还不够,你所学到的,还过于碎片化,这世间许多事,不是靠一两个临时拼凑的认知,就能看透的。”
“什么是碎片化?”
“就是接受的知识大多是短小的,零散的,也就是书读得不够。”赵宁很耐心地跟他说着,“书读得越少的人,越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狭隘偏激,而且固执。”
说着说着,父子二人已经到了福宁宫。
下面的人准备了饭菜。
赵瑾很有礼节地对赵宁行礼,吃饭的时候非常规矩,一定要等赵宁先动筷子,他才动。
赵宁颇为惊讶:“瑾儿,这些都是谁教你的?”
“母亲教孩儿的。”
赵宁哑然失笑:“平时吃饭,倒不至于如此。”
“爹爹,那我们到底是否应该征讨日本国呢?”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赵宁笑了笑,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赵瑾便开始用膳,整个过程他没有再说一句话,哪怕一个字。
等吃完后,他又行了礼。
赵瑾是一个非常懂礼数的人,一板一眼,每一个动作仿佛都有考究。
“父亲,孩儿来找您,其实还有一些不情之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