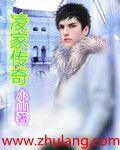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毒妃狠绝色邪王轻点撩 > 矫情和自尊(第2页)
矫情和自尊(第2页)
萧绝自知理亏,却不会在丫头面前认错,崩着脸一声不吭。
紫苏还想再说,杜蘅轻声道:“你先出去。”
老实说,他一声不吭地溜走,剩自己孤零零一个人独对陌生的环境,面对尴尬的处境,心里的确不舒服。
可她不是孩子,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任『性』地发脾气,让他下不来台。何况,昨天的事,她的责任其实更多一些。
“走吧。”白蔹如蒙大赦,赶紧把杜蘅扶到炕沿坐下,拉着紫苏急急地退了出去。
“阿蘅~”萧绝弯下腰,轻轻碰了碰她的额。
杜蘅垂着眼,没有闪避却也没有说话,红晕渐渐漫过耳际。
萧绝瞧着她娇娇怯怯的模样,逸出一抹愉悦的浅笑,低低的声线,温柔中夹着几分怜惜几分骄傲:“还疼吗?”
不等她答,又越发凑近了些,以耳语的音量,小小声道:“我去寻了『药』膏来,一会抹一点,应该会舒服很多。”
杜蘅吃了一惊,猛地抬头看他。
“放一百二十个心。”萧绝唇角微勾,低笑道:“没有惊动钟翰林,也不是问我娘讨来的。”
杜蘅咬着嘴唇,脸红得似火烧:“谁,谁问你了?”心里,到底松了一口气。
萧绝顺势将她半搂在怀里,大掌伸了进去,岂料刚一触到肌肤,杜蘅已疼得哆嗦了起来,他不禁着急,想也不想撩了裙裾:“我看看……”
杜蘅大惊,死命按住他的手:“不许看!我自己来~”
萧绝也不勉强,把『药』膏往她手里一塞,吩咐人送了热水进来,亲自拧了『毛』巾递到她手里:“给。”
杜蘅捏着『毛』巾,却发现处境更加尴尬。
萧绝就坐在她身边,笑眯眯地看着她,半点想要回避的意思都没有。
杜蘅瞪着他,脸上红云越来越盛,终是憋出二字:“出去。”
萧绝微微一笑,拿回『毛』巾,伸进去擦拭了起来。
“咝~”杜蘅来不及羞赦,就被那疼牵走了心魂,脱口求饶:“轻,轻点。”
萧绝眉一皱,把『毛』巾扔回铜盆,一手按着她的腰肢,另一手飞快地褪下了她的亵裤。
杜蘅低嚷一声,羞得闭紧了眼睛往他怀里一钻,当了驼鸟。
细腻白皙的肌肤上遍布着点点青紫的瘀痕,大腿内侧有红肿了一片,触手烫手,显见擦伤得很严重了。
他错愕万分,一时真不敢相信那些伤痕竟都是自己造成的?
懊恼如『潮』水袭来。
他二十三了,自己又经营着青楼,年少轻狂时乏人管束,亦有过一段荒唐岁月,自然不是那十几岁未经人事的『毛』头小伙子。
更何况,他对自己的自制力向来极有信心,绝对可以收放自如,收发由心。
是以,他可以在长达二年的时间里,对她发乎情,止乎礼。
却没有想到,昨夜居然失了控,表现得比刚开荤的『毛』头小子更鲁莽!
这对他,绝对是一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