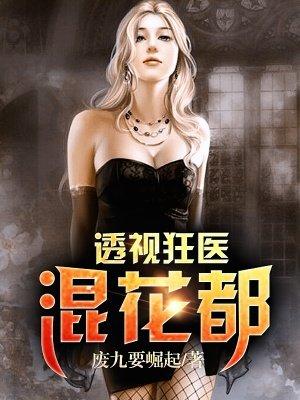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老干部穿成反派妻主后(女尊)全文百度 > 第11章 011(第1页)
第11章 011(第1页)
等谭柚跟沈御医离开后,硃砂着人将热水送进来,胭脂挽起袖筒用襻膊绑着,浸湿毛巾给司牧擦洗身子。
司牧体虚,这会儿直接进浴桶里泡热水澡说不定会晕过去,只能先凑合擦擦。
“永乐宫那边如何?”司牧慢条斯理地拆开油皮纸,露出里面麦芽黄色的饴糖。
糖块在他裹着纱布的手心里握了好一会儿,如今散发着丝丝缕缕甜香,很是诱·人。
胭脂弯腰拧水,“说是一切如常。”
司牧眼睫落下,声音叹息,语气带着淡淡幽怨,“我不在,她们应该极其畅快。”
天色已经暗下来,勤政殿内早已掌灯,暖黄色光泽落在司牧白皙的身子上,像是黄昏时的光线沐浴着珍珠,散发着盈盈润光。
可惜本来完好的珍珠,因为跌倒身上磕的青一块紫一块,最严重的部位要数膝盖跟小腿。
胭脂看的心疼,比磕在自己身上还难受。
尤其是他直起腰后看见司牧手里不知道打哪儿拿了块饴糖,剥开油纸正要往嘴里送,不由出声,“殿下,这糖?”
胭脂脸色认真,神情紧张,生怕再出半点差池。
“谭翰林给的。”司牧将糖放进嘴里,朝胭脂一笑,“无碍,这应该是她从太傅那儿得来的。”
胭脂这才松了口气。
谭太傅历经三朝,在司牧跟司芸年幼时曾担任过帝师,负责教导她们功课。若是谁表现的好,谭太傅就会像变戏法一样,从手心里变出一块糖来奖励她们。
从小到大,司牧得到的糖总是最多。
熟悉的甜香充斥着口腔,司牧才觉得嘴里喝完药的苦味慢慢淡去。
太傅自然是极好的,可惜老太太在官场多年,做事总是不偏不倚小心谨慎,甚至为了谭家,甘愿把独女外放它省做官历练,都不愿意将不争气的女儿留在京城享受她的庇荫。
对于司牧来说,谭太傅在他跟皇姐间不偏不倚圆滑中庸,那便还是有所偏倚。
沐浴完换了身衣服,司牧从里间走出来。
硃砂已经等在外面,行礼说,“主子,‘老鼠’找到了。”
司牧不相信这世上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前脚他打算对谭橙用药,后脚就有人快他一步对他下手。他这殿内定是有了外心,将消息送了出去。
司牧洗漱的时候,把这事交给硃砂去办。短短不过小半个时辰,人就被揪出来。
司牧坐在绣墩上,看着面前送过来的药膳,没有半分食欲,秀眉拧起,情绪也跟着低迷,有气无力地问,“可查清是谁的人?”
硃砂望向司牧苍白的脸色,低声道:“查清了,是太君后的人。”
司牧捏着汤勺的手微微一顿。
勤政殿被司牧管的很严,这些年后宫几位贵君跟君侍不是没有胆大包天想送人过来探听消息的,奈何勤政殿铁桶般滴水不漏,根本进不来。
若不是今天这事,硃砂可能还不会发现一直有老鼠藏在铁桶里面。
硃砂道:“对方是您刚搬来勤政殿时便在了,这些年都在跟太君后私下传递消息,只不过说的都是您的喜好跟平时日常,没有别的。”
司牧眼睫垂下,手指捏着勺柄轻轻搅拌碧青色碗里的药膳,声音听不出情绪,“那我真是要谢谢父君对我关心呢。”
他懒得自己吃,索性搁下勺子,昂脸看向胭脂。胭脂上前两步,端过药膳喂他。
“将人送去太君后殿内,其余的话一个字都不要说。”司牧看着自己包裹着纱布的掌心,听着外面随风飘来的淡淡丝竹管弦声,垂眸笑,“你看,我还是太心软了。”
胭脂跟硃砂低头不敢说话。
永乐宫的宫宴到戌时才结束,本该是以长皇子为主角的选驸马宫宴,结果因为小插曲,变成了君臣同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