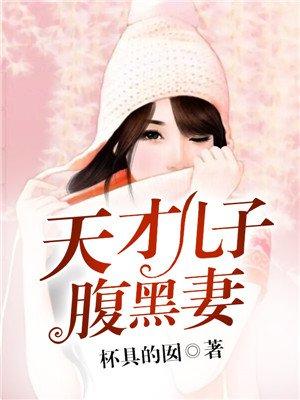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皇姑是什么意思 > 第148章(第1页)
第148章(第1页)
他仰起头,似乎深吸了一口气。过了片刻,又听他低低地唤了一声:“颖坤。”
颖坤埋头往伤口敷药:“臣在。陛下有何吩咐?”
许久都不闻他再开口,她刚要抬头去询问,却听见他用近似呢喃的低语叫了一声:“末儿……”
他离得太近,颖坤一抬头就和他撞到一起,而且撞的地方……好巧不巧。
她急忙后退避让,脑后却被一只手扶住了,他迫使她仰起脸来,侧过脸印在她唇上。
这下她也无法说服自己只是碰巧撞到了,伸手推他,双手却正好按在他赤|裸的胸口,掌下肌肤热烫,心口撞如擂鼓。她立即把手缩回来,更被他搂紧拉向自己。他急切地含住她的双唇,舌尖从她唇上扫过,钻进去撬她牙关。
颖坤大骇,手下使了十二分的力气才将他挣开。她跪在地上连退数步,双手高举过顶:“陛下!”
兆言不肯罢休,衣衫不整从榻上站起来拉她。颖坤拜伏于地,更加抬高声音:“陛下!”
他终于停下,声音却还颤栗不稳,呼吸急促:“末儿,我忍不下去了,我只要一看到你……”
颖坤心头也在狂跳,强自按捺住用冷静的语调道:“看来陛下确实是因为贵妃有孕旷居已久……”
“旷居已久?”他怒而失笑,“朕难道还缺女人吗?我看到其他女子有忍不住吗?”
她只是想找个借口让彼此都有个台阶可以下而已,听到这话不由皱眉,复又拜了一拜:“臣叫人进来侍候陛下。”转头对外扬声道:“齐大官在吗?请进。”
齐进在外头应道:“哎!”刚要入内,又听见皇帝厉声喝止:“谁都不许进来!”他伸向帐门的手只好缩了回去。
兆言看向五体投地拜倒在自己脚下的人,她的额头叩及地面,面目全不可见,她的举止已经表明了她的态度意愿。他起得太急,伤口似乎又裂开了,左肋下一直到心口都撕扯般得疼痛。他颤声道:“末儿,你抬起头来看看我……”
颖坤伏地许久,心绪已渐渐平复稳定,叩首后直身抬头,却不看他:“陛下,我是您的姑母,也是姨母,长幼有序。”
“又不是嫡亲的!我对你这么多年的心意……难道都抵不过一句长幼伦理!”
又不是嫡亲的,这句话他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说了?起初以为只是由于她年龄与他相仿,小孩子心气别扭不肯认她做长辈,原来竟是为此。
这么多年的心意,往事纷至沓来,许多当时不以为意的小事,现在忽然都变得通透明白。就连最近回洛阳后这段时间,就连今日,他的种种奇怪举止也都有了解释。
想通之后,她的心情却更平静,冷然道:“陛下说这些话的时候,可有想过已故的贞顺皇后,想过皇宫里为陛下诞育皇子而正卧床养胎的贵妃?”
他颓然跌坐回榻上,举手掩面:“我以为……我都已经死心了,你为何还要回来?你就留在雄州,再也不见,再也不念,一辈子也就过去了。你为何还要回来?!”
颖坤道:“臣回洛阳是因为母亲病重,可不是为了勾引陛下。”
兆言放下手盯着她:“你站在我面前,就是勾引我。”
颖坤霍然起身:“那臣以后都不会出现在陛下面前。”
兆言喝道:“你站住!”她充耳不闻,掀开布帘跨出帐外。齐进一直守在门口,笑着迎上来:“校尉怎么出来了?陛下……”
颖坤道:“还是齐大官进去侍候陛下吧。”
齐进举起裹着纱布的右手,面露难色:“可是小人的……”
颖坤冷冷瞥他一眼,他后半句话就说不出来了,讪讪地收起笑容,转身入帐。
颖坤不顾营中守卫挽留询问,牵了一匹马连夜疾驰回离宫。她与七郎下榻处相邻,七郎已经回来了,看到她焦急地问:“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说一声就跑不见了,你知道我多担心?陛下呢,不是说今夜留宿外营,怎么你又一个人回来了?”
颖坤道:“陛下有伤不良于行,我就自己先回来了。”
七郎跟在她身后进屋,小心问:“你们俩走失在野地,陛下没有……对你做什么吧?”
这句话让颖坤回过头来,目光凌厉地盯视他:“七哥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七郎心虚,嗫嚅道:“那么明显,你自己觉察不出来吗……”
颖坤深吸一口气吐出,问:“七哥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十二三年前吧……”
十二三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十岁出头的孩童,那么久远。她心中纷乱,把早间抵达安置在房中的行装又收拾起来:“七哥,这儿的事你安排吧,明天一早我就回洛阳。”
☆、第四章章台柳1
颖坤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提前辞别回洛阳。家中母嫂不禁惊讶,只去了一天就回来,她随便编了个理由搪塞过去。七郎则随驾留在清河苑狩猎练兵,过了月余才回还。
颖坤一直留在家中侍候母亲,闭门不出。逃离了清河苑,连知情的七郎都见不到,她却并没有觉得心安。那天的情景反复在脑中盘旋,她一想起兆言的名字,首先映入脑海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是少时亲厚的玩伴,而是那晚他迷乱失控的面容和眼神。她甚至还记得他胸腹间的肌理,记得那奇异萦绕的气息,记得他的舌尖从她唇上扫过的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