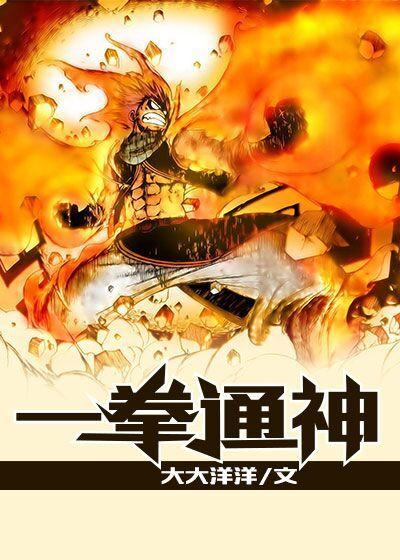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朕饿了 卷二 > 第195章(第1页)
第195章(第1页)
可是她醒来时还在床上!
胶东王的解释是,「夜里已经冷了,你踢了被子。」
素波不禁生了警觉,「难道你不要睡觉的吗?」
胶东王本来要说怕王妃着凉,突然灵机一动,「我自己一个人害怕。」
噢,原来是这样!素波的圣母心立即泛滥了起来,是的,别看胶东王慢慢懂事了,但其实他的内心还是个孩子呢,可怜又可爱的孩子。
于是经历了几番周折,素波又回到了床上。此时已经进入了初秋,白天虽然还很热,但是晚上却渐渐变凉,毕竟还是大床上舒服又暖和。更重要的就是胶东王虽然长大了,但他本质还是一个单纯无害的少年,自己根本不必防着他。
胶东王不知道王妃给他的评价是单纯无害,但他的确顶着一张单纯无害的脸将文澜阁大大的变了样子。不,确切地说,是相府。
文澜阁最初就建在相府之内,后来陆相交出文澜阁时,便将文澜阁处一带划出,与相府隔墙而立。胶东王接掌了一段时日后,便上奏皇上另为丞相择一府第,将原来的相府全部划归文澜阁。毕竟几年时间经过不断地扩建,文澜阁不论是书籍、器物还是人员都一直在增加,先前的房舍已经很拥挤了。而相府分出了文澜阁一处,府第也变得狭小不便。
说到底,当初将文澜阁建在相府之内,其实就是朝廷草创时的权宜之计,如今文澜阁的重要性日渐突显,原来的布局早已经不能适合现在的需要了。
胶东王还在奏折里提出要在文澜阁兴建太学,那就更需要一定的房舍,而将相府与文澜阁分开就是势在必行的。
这份上奏得到了朝中大部分人的赞许,消息传出,京城之中的儒生们首先纷纷上书请建太学,接着京外亦传来如雪般的上书,天下儒生都盼着太学早日成立。
陆相身为文臣之首只能特别赞同,他在朝堂上慨然应答道:「纵是老夫带着家室子女风餐露宿于外,只要能见到儒生们在太学读书就心甘情愿!」可是他回了相府关了门便大骂道:「好个胶东王!为沽名钓誉,竟欺负到外祖父头上了!他究竟是不是真傻?」
陆相的密室之内坐着的人很少,有光禄勋张宗;陆相的长子陆子腾,他还在司州刺史任上,此番因运送粮草进京;张宗的长子也是陆相的孙女婿张慎行;还有如今任文澜阁主薄的许衍。
大家听闻一向谦和的陆相竟然发火骂人,赶紧都站了起来,「丞相息怒。」
陆相一时气恼,转霎便控制了心境,「你们都坐吧。我不过在你们面前随意些,说几名心里话罢了。」
张宗躬身一礼方才坐下,也道:「无怪岳父生气,文澜阁是岳父费了多少心血才建成,如今有这么大的规模,这么高的影响力,竟让胶东王一声不吭地算计了去。且他又得寸进尺,还要岳父的府第,我在朝堂上听着亦觉得可恨!」
陆相的长子陆子腾便道:「父亲和舅兄且宽心,纵是丞相府做了太学,皇上定然另给相府赏一处好宅子。」
张宗就说:「子腾,你原不在京城,此事的来龙去脉并不大清楚。岳父岂是在意这一处宅子?便是皇上不赏下新宅,岳父还真能风餐露宿了?丞相生气的是胶东王算计了他,非但占尽了好处,还让皇上和天下人以为他的上奏是陆相的主意‐‐偏偏陆相还没有办法反驳。」
「说到这里,我其实也有一事不大明白,胶东王到底是不真傻了?」当初胶东王住在陆府时,陆子腾一直在司州任职,并没有亲眼见过这个外甥,但此次回朝见了几面,觉得胶东王虽然好静少语,但完全是一副贤王的举止,「该不会大家弄错了吧。」
「再不可能弄错的,」张慎行站起来道:「胶东王出宫后在相府住了整整一年,白天与我们在一处读书,晚上回到内宅,相府这么多人都看在眼里,他就是个傻子!」想了想又补充道:「今日辰弟没来,他与胶东王在一起的时日更多,比我还清楚。」
虽然是亲儿子,可是陆子腾倒还知道陆辰是个什么样的,便斥道:「辰儿的话哪里可信!他整日说别人是傻子,我看他才是个傻子呢!」张慎行也不过比陆辰大上一两岁,家里有大事已经让他参与了,而陆辰还不知道家里有这间密室。
许衍见张慎行不好再说话,便赶紧起身道:「大人,张公子所言并不错。先前我曾陪胶东王读书,见他虽然看起来相貌出众、举止不凡,又有过目不忘的读书天分,但用膳、言谈、起居等等都与常人不同,都要靠身边的内侍提点。」
陆子腾就道:「胶东王生长在深宫内院,不会打理日常琐事,皆要内传服侍倒也没有什么。」
「也不只是不会打理日常琐事,」许衍就将胶东王日常的一些怪诞行为讲了出来,又道:「虽然胶东王能过目成诵,但其实他并不懂得其中的深意,就似鹦鹉学舌一般。」
张宗也说:「我们也曾在宫里打听,原来胶东王小时候极聪颖的,后来生病后就变成了这样,只是静妃娘娘一直极力掩饰,因此皇上才没有发现。」
提到了静妃,陆子腾心里颇不是滋味儿,他一向与大妹妹情分极好。当年父亲若是能施以援手,也许自己的妹妹就不会这样早就香消玉殒了,而她的几个孩子也不会落得现在的结果。但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陆子腾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管怎么样,胶东王总是我们家的外孙,如今他接手了文澜阁总算是落到自己人手中,将来太学建成,我们陆家也一样跟着荣耀,并没有什么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