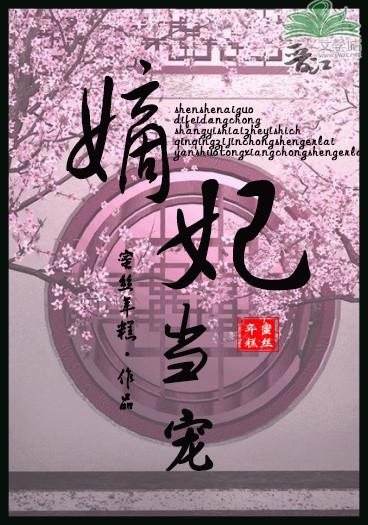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蚱蜢的拼音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这也是骗人的。毋寧说戒指变松了。铃木比结婚当时还瘦,只要一个不留神,戒指就会弄丢。每当那种时候,他总会想起亡妻的话,浑身哆嗦。「千万别弄丢了戒指。」生前的她曾经郑重地对他说:「看到戒指,就要想起我唷。」要是丢失了戒指,亡妻地下有知,一定会大发雷霆。
「我来猜猜看。」比与子的眼睛亮了起来。
「就跟你说这不是猜谜了。」
「你太太八成是被那个蠢儿子害死的,对吧?」
為什麼你会知道‐‐铃木拼命压制住就要探出去的身子,仿彿自己下一刻就会眼神游移,喉结抽动,眉毛颤抖,耳朵发红。要把持住,是一件至难之事。内心的动摇仿彿随时都会从身体的孔穴溢流而出。
同时,铃木脑裡浮现被压溃在休旅车与电线桿间的妻子身形,他慌忙甩开这个画面,腹肌使力,问道:
「為什麼寺原社长的儿子要杀我太太?」
「正因為他不需要理由就能杀人,才会被叫做蠢儿子嘛。」比与子一副「你明明知道」的表情说:「蠢儿子到处惹事生非。半夜偷车飆车是家常便饭,喝醉撞死人更是一年到头都有的事。」
「太过分了。」铃木不带感情地说。「真是太过分了。」
「就是说啊。十恶不赦呢。那,你太太的死因是什麼?」
「不要随便把人傢说成死人好吗?」
铃木忆起了亡妻被辗过的身躯,以為早已抹灭的记忆轻易地、鲜明地復甦。他仿彿又看见她浑身是血,鼻樑扭曲,肩膀的骨头被压得粉碎。铃木呆立在现场,听见一旁跪伏在路面的中年交通事故鉴定人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这不只是没踩煞车,根本是故意加速的。」
「是被车子撞死的吧?」比与子一语中的。
没错。「妳不要擅自决定好吗?」
「如果我记得没错,蠢儿子两年前撞死的女人,就姓铃木。」
这也没错。「骗人。」
「真的。我常听蠢儿子吹嘘他的英勇事蹟。」
英勇事蹟‐‐这种形容让铃木勃然大怒,可是如果对她的话做出反应,就等於一脚踏进了圈套。
「不管蠢儿子再怎麼為非作歹,也不会受到惩罚。你知道為什麼吗?」
「天知道。」
「因為有人袒护他。」比与子扬起眉毛。「父亲跟政客。」
「就是刚才说的税金跟僱用保险的道理?」
「没错。总之,你知道杀害你太太的蠢儿子还逍遥法外吧?所以特别调查他的事,发现那傢伙在父亲经营的公司工作,也就是『千金』,所以才会以约聘员工的身份进公司。」比与子背书似地流畅说道。「就是这麼一回事吧?」
「我何必大费周章做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