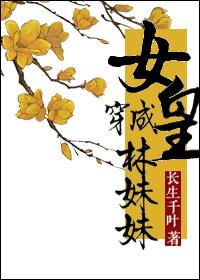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城邦暴力团写的什么 > 第104章(第1页)
第104章(第1页)
&ldo;废话你他妈不会看哪我瞎子啊!&rdo;光头嘴巴上还叼着烟,眼像是给熏得睁不开,可是别有一股睥睨万教的糗霸王气势。
孙小六这时踏着大步过来,边走边昂声喊道:&ldo;跟你说今天不玩,散了罢,我讲的是法国话吗?&rdo;
穿拖鞋的应声退了几步。光头倒显得沉着得多;一面仍瞄着我,一面倒像是答复着孙小六的话:&ldo;今天我们也没工夫玩‐‐倒巧了,我们要办的货在你手上。&rdo;说时一拍前座的肩膀,那骑车的兜手一提,抬起车把手,将前轮朝我脸上一挺,我跳两步退开,膝盖弯却杵在另一辆机车的轮盖上。光头这时吐掉半截烟头,冲我一抬下巴:&ldo;你叫张大春是罢?&rdo;
&ldo;怎么样?&rdo;我哑嗓子硬硬还了一句,腿已经打起抖来。
&ldo;怎么样?我他妈还叫张大千呢!你妈怎么样?&rdo;说时左臂往下一挥,把报纸套子甩落,当下露出一把二尺四,右手再一拔,青光出鞘,人也跳下车来,同时刀尖朝孙小六一指:&ldo;抱歉!是本堂的任务。你小子心情不好就更不必管这档子闲事。&rdo;
偏在这一刻,从西藏路那头蹿过来一条黑影‐‐更准确一点地说,是从两辆挡在青年路中央的机车之间蹿过来一条黑影,直奔我跟前,一直到它停下来坐定了,我才看清楚:是一只名叫水塔的洛威拿。它之所以叫水塔乃是因为它的主人徐老三不会念英文,却给起了个英文名字叫sweetheart。水塔坐在我和光头之间滴口水的那一刻,两辆机车&ldo;哐哐啷啷&rdo;向两边倒去,穿一袭黑风衣的徐老三出现了。他也穿着拖鞋,时不时还从敞开的风衣下摆里露出蓝白条子的棉质睡裤。显然,他是出来遛狗的。
&ldo;吵什么啊?小朋友!都几点几分啦?家里没大人了吗?&rdo;徐老三一路走、一路朝左右张望,先看见孙小六时顿了顿,道:&ldo;我你小子又回家啦?&rdo;再看见我,则皱了皱眉,好学生怎么也跑出来跟他们撂狗链哪?&ldo;最后,他的视线停在光头脸上,看了足有十秒钟,才沉沉问道:哪里的?&rdo;
&ldo;竹联孝堂,&rdo;光头手里的二尺四晃了晃,垂下地去,继续说,&ldo;有点事情在处理。你‐‐&rdo;
一个&ldo;你&rdo;字才出口,徐老三的一只巴掌已经反摔在光头的脑壳上,这一下风衣大开,里面的蓝白条睡衣居然和底下的睡裤是成套的‐‐可是他右手臂连肘端着的东西却吓得我膀胱猛地一紧;这算生平仅见,是一柄双管霰弹枪。枪口正杵上那光头的嘴巴。徐老三仍旧不疾不徐地说道:&ldo;什么你呀我呀的?&rdo;接着枪管撩个小圈儿,往那脑壳儿上非常非常之轻地点了三下:&ldo;记住!徐。三。哥。叫你们回家去了。孝堂?还他妈哭堂呢!&rdo;
光头无可奈何收刀入鞘,恨恨地看了我一眼,转脸又想跟徐老三说些什么,不料徐老三居然一挺右臂,朝红绿灯开了一枪,那枪声不像电影里常听到的那样响,可是音波撼动,果然荡胸震腑,几乎就在枪响的同时,水塔没命似的狂吠起来‐‐事后很久我才想到:这绝对是经过训练所致,徐老三一举枪,水塔就吠,吠声掩过枪声,不在场的谁也不知道徐老三干了什么恐怖的勾当。&ldo;你还有话说?&rdo;徐老三把红灯、绿灯、黄灯罩子轰了个漫天花雨之际,跟那光头所说的最后两句话是:&ldo;去跟你们老大说,他连听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呢!&rdo;
等这帮什么竹联孝堂的瘪三们点火催油、呼啸离去之后,徐老三把枪插回风衣内侧一个fèng在夹帛上的长皮套子里,又一颗一颗、动作非常缓慢地扣上扣子,低着头像是在解释什么似的跟我们说:&ldo;没法子,我已经太久不混了,现在什么鸟鸡巴都跑出来了。你们没事罢?怎么会惹上人家的?&rdo;
我看看孙小六,孙小六看看我‐‐事实显然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孙小六认识他们,而且&ldo;陪他们玩&rdo;过;不过他们却是指名来找我的;而我却从来没见过他们。结果我和孙小六异口同声说:&ldo;不知道。&rdo;我还加了句,&ldo;他们说我是他们要办的货。&rdo;
&ldo;如果真是孝堂,那你漏子就捅大了。&rdo;徐老三说着咬嘴打了个唿哨,朝西藏路方向一指,水塔耀武扬威地撒腿往回冲。徐老三则继续说下去:&ldo;他们今天堵不到你,明天还会来;在村子里堵不到你,就会在路上等。你要不就别出门,要不就闪远一点。&rdo;
老实说,在这一刻,我还想不到&ldo;可不可以不出门&rdo;或者&ldo;闪到哪里去&rdo;之类的问题。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红莲‐‐也许红莲是他妈那个什么竹联木联的某个老大或老二的女人,被我不小心搅和上了,人家不慡,就吆喝了这样一票牛鬼蛇神来砍我一条脚筋。我能想到的只不过如此而已。
&ldo;你没有去搞政治罢?比方说党外那些养的东西,或者之类的‐‐&rdo;徐老三抬眼瞄了我一下‐‐他的眼眶呈三角形,刚要扬起来的上眼皮不知怎么给往下削了,所以表情总透着些不得伸展的忧恼。有人说见过鬼的人的眼睛就会逐渐长成如此形状。这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从来没正眼瞧过他,但是当他这样瞄着我的时候,我却从那双三角眼里看见一些比见鬼还要不安的东西‐‐一时说不上来,总之是很惶惑、很焦虑的一种情绪,这让我突然感到有些温暖。他接着问道:&ldo;还有,我想你也不会去搞这个罢?&rdo;说着,他用大小拇指靠嘴边比了个吸烟斗的姿势。我知道,电视剧里出现了这个手势就是有人在吸毒的意思。
我摇了摇头。
&ldo;出动这么一大批人马,找上你这么个书呆子,的确有点奇怪;不不,的确很奇怪。&rdo;徐老三说,随即扭头望一眼孙小六,&ldo;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rdo;
&ldo;前两个月我和他们里面的几个干过一架,可是好像没什么‐‐他们今天就是来找张哥的,&rdo;孙小六搔搔头皮,道,&ldo;而且还说是什么本堂的任务。&rdo;
&ldo;我肏!那累了。&rdo;徐老三从风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掏一支叼在嘴里,用那支老式的银质磨轮打火机打着,吸两口,喷出一条可谓&ldo;直冲牛斗&rdo;的白烟,才慢条斯理地说,&ldo;书呆子最好还是逃命去罢。&rdo;
31启蒙的夜
坦白说我并不知道这一次逃命之旅终于何时何地‐‐因为截至我目睹孙小六从五楼窗口一跃而出、奔往竹林市去,同我正式分道扬镳的这一刻为止,我都不能确信,一切已经过去了、安全了,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就恢复平静了。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我必须这样假设,才敢于继续回忆下去:从一九八二年冬天的那个夜晚开始。
和我可以说没有半点交情的徐老三在这天晚上给我上了一课。他先叫孙小六溜回家去,想办法把他姊叫出来,再同我们到村办公室集合。孙小六临去之时我是颇不以为然的,嘟囔了一声:&ldo;叫她干吗?碍手碍脚的。&rdo;徐老三瞪了我两记极尖极大的三角,道:&ldo;没有小五,你活不到一个礼拜。&rdo;